首页>人物·生活>秀·风采秀·风采
沈苇:我的新疆我的梦
——从“新疆三部曲”谈起
□演讲人:沈苇
■演讲人简介:
沈苇,诗人、散文家,现为新疆文联《西部》文学杂志总编、中国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委员,1990至2000年曾在《亚洲中心时报》工作。著有诗集《沈苇诗选》、《沈苇的诗》(维汉双语版)、《博格达信札》、《新疆诗章》、《在瞬间逗留》等8部,散文集《新疆词典》、《植物传奇》、《喀什噶尔》等6部,评论集《正午的诗神》等2部,另有编著和舞台艺术作品多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刘丽安诗歌奖、柔刚诗歌奖、十月文学奖、花地文学榜年度诗歌金奖等。
沈苇
编者按:
新疆,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它是历史上著名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西部地区开放的前沿。其神奇美妙的少数民族风土人情为人们所向往。本期讲坛邀请在新疆生活20余载的著名作家沈苇先生用如诗的笔墨讲述“新疆故事”和他笔下的新疆。
■精彩阅读:
□这些故事里有人,有人的状态、人的言行、人的命运,构成一种多民族融汇的“精神地理”。
□我们的写作,仅仅“以忧解忧”是不够的,要超越焦虑、忧虑,去祝福,诗歌要走的路很漫长。
□这样一种力量,能改善我们内心,抵御种种野蛮裹挟,免于心灵碎片化、齑粉化。因为我们需要有这样一种力量更加有力地说出“是”!
《新疆词典》
引言:
这个演讲与我生活了20多年的新疆有关,也与我新近出版的《新疆诗章》、《新疆词典》及《新疆盛宴——亚洲腹地自助之旅》有关。新疆是亚洲的腹地,是地球上离海洋最远的地方,美国地理学家埃尔斯沃斯·亨廷顿在《亚洲的脉搏》一书中用“亚洲心脏”称呼新疆,塔里木河则是亚洲的心跳和脉搏。那么,在这片亚洲的腹地上,有着怎样的“精神地理”呢?
我理解的“精神地理”,既是一种地理气象,更是人的精神,是人和地理融合后的气质与个性。“精神地理”无疑与地方性、地域性、边缘与边疆等概念有关,也与现代性、当代性、时代性有关。“精神地理”由地域中的人来呈现,也由写作者来发现。换言之,“精神地理”就是一种与地域有关并超越了地域本身的文学精神。
我对自己30多年写作生涯的评价是:失败的小说写作,持续的诗歌创作,还可能是一个额外的散文家。在浙江师范大学读书时,我写过4年小说,我不认为我是成功的。然后我改写诗歌。从诗歌转向小说的人很多,但从小说转向诗歌的十分罕见,英国小说家哈代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大学毕业后,我去了新疆,那是1988年。当时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到了新疆,觉得不写诗就白来了。在我看来,群山草原、戈壁沙漠,缺少故事和细节,却有着抒情的“资源”,新疆的荒凉与灿烂,就是诗的直喻。而我写散文,是写诗之外的额外收获,《新疆词典》写作了10年,就是一个额外收获。
作为不太会讲故事的人,我先要讲几个小故事。
新疆的故事新疆的人
维吾尔阿希克的故事。阿希克,翻译过来就是“痴迷者”的意思。这是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游走群体,手摇萨巴依(一种乐器),乞讨、歌唱、修行,有点像游方僧。我曾去过喀什附近的协合力村做田野调查,那个村里阿希克很多,还有割礼师傅和卖草药的,都是游走天下的人。男人一成年就得离开村子,这是由村里土地资源少造成的。这里讲的是住在喀什吐曼河边麻扎(墓地)里的两位阿希克。他们是好朋友,约定白天找到的食物,晚上回了墓地要一起分享。那天,一位阿希克向东去了,另一位向西去了。向东去的阿希克讨得一个馕饼回到墓地,久等另一位阿希克不见回来,实在饿得不行,就把馕偷偷吃了。等另一位阿希克空手而归时,这位阿希克撒了谎,说自己也没讨到食物。两人便睡了。半夜里,偷吃了馕的阿希克十分不安,难于入睡,当听到他的朋友在梦里喊饿叫苦时,便悄悄起身,竟然跳进吐曼河自杀了。
哈萨克牧民的故事。哈萨克是一个跨国民族,哈萨克斯坦有1700多万,新疆有150万左右,他们生活的牧村叫阿吾勒。话说北疆一牧村的哈萨克人从未去过北京,有一位牧民的儿子考上了北京一所大学,牧民终于陪着去了趟首都。等他回来,如同英雄凯旋,大家围着他,问这问那。这位牧民说,北京到处是高楼大厦,汽车多得很,像拥挤的羊群。说到后来,他轻叹了口气,说,北京好,好得很,但可惜啊,对我们这儿来说,太偏僻了。我很佩服这个牧民,觉得他非常幽默。
兵团人的故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功勋卓著,现有人口近300万,主要是汉族。早期开发者很苦,住地窝子,在戈壁滩上开荒、种地、筑城,强体力劳动,许多人学会了边走路边睡觉,掉到坑里爬起来,继续边走路边睡觉。我的故事讲的是“中国长绒棉之父”陈顺礼,他是湖南人,父亲早逝,母亲独自拉扯他长大,他后来支边到新疆兵团农场,30多年只回过老家一次,见过母亲一面。后来他得了癌症,临终前想到这一点,就一直在哭,最后的力气都在哭泣中……
瑞典修女的故事。瑞典和新疆、中亚的缘分,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编年史中的一个误会,书中说“瑞典人来自喀什噶尔”,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极大地激发了瑞典人探索新疆的兴趣。1894年,瑞典中亚传教团将总部从高加索迁到新疆。后来来了一批瑞典探险家,最著名的是发现楼兰的斯文·赫定和发现小河遗址的贝格曼。洛维莎·恩娃尔(1865—1935)1913年到新疆,在库车、沙雅等地22年,后来她变成了一名“赤脚医生”,背一个药箱,东奔西走,为人们看病。70岁那年,她感觉到自己快要死了,打算离开新疆。她骑马翻过天山到了塔什干,从塔什干坐火车到莫斯科,准备从莫斯科回瑞典,结果死在塔什干到莫斯科的火车上,葬在俄罗斯著名的新圣女公墓。我为她写过一首诗《无名修女传》。
这几个故事讲的是新疆这片土地上的人,或者曾在新疆客居过的人。阿希克的故事,讲的是信誉、良心、内疚和羞耻感。哈萨克牧民的故事,表现了牧民的朴素和幽默,使人想起一句话:“你身在哪儿,哪儿就是世界中心。”“长绒棉之父”的故事,讲的是故乡与亲情、思乡与还乡。瑞典修女的故事,讲的是热爱与融入。
这几个故事表达着我对新疆的“体验”,这些故事里有人,有人的状态、人的言行、人的命运,构成了一个多民族融汇的“精神地理”。我对新疆的体验是复杂和深刻的。一方面待了27年,感到已融入这个地方,变成了他乡的本土主义者;但另一方面,心里也有困扰。可以说,亲近感和陌生感同在。这也许就是我书写新疆的一个动力吧!
不要被风情和风景所遮蔽
现在,新疆在某种程度上被风情主义和风景主义遮蔽了。
首先,我认为,是这个地方的“自我表述”没有表达好。前一段,我们总用“魅力新疆”这个字眼,到网上一查,全国从省区、地市到县市、乡镇、行政村、村民小组,有300多个魅力地方,这等于什么都没说。而旅游者作为外来者对新疆的描述,不外乎歌舞之乡啊,瓜果之乡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啊,边疆处处赛江南啊,等等,都是印象式的,只触及了新疆的皮毛。所以有人说得好,“旅游就是从自己活腻的地方到别人活腻的地方去”,尤其要到别人可能还没活腻的边疆、边地去,因为那里好玩啊。人们现在有了点钱,进入了“全民旅游”时代,可以无限地消费远方了。还有历史的原因,从从前的荒远之地,到上个世纪初发现楼兰后的西部探险热,再到新世纪以来中国最具魅力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我认为,新疆正在经历一个被审美化、被消费化的过程。它是一个被“看”的对象,一个被观赏的对象。我现在在使用“西部”、“西部文学”、“西部诗人”等概念时,都为它们打上了引号,目的是“解构”它们。我不承认自己是“西部诗人”,只是一个此时此刻生活在西部的诗人,我也不想写出范式化的“西部诗”,只想写出几首好诗,或者几行好诗。这就涉及到了写作的问题,目前大量的人文地理写作,需要一问的是:我们的文学,真的触及了这片土地的本真和生命了吗?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
有一个词语叫“误读”。现在我去内地,常遇到有人问我新疆安不安全的问题。我会坚定地告诉他们:新疆是安全的。新疆处于一个很艰难的时期,这是一个心理问题。显然,对新疆缺乏了解和理解的人,对此存在“误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新疆视为“麻烦”的同义词,情感上加以紧急删除;二是暴恐事件出现后,很多日常性的东西被遮蔽了,偶然事件被放大了。听说现在许多人不敢去新疆,我觉得大可不必。想想看,50多个民族、有2000多万民众还在那里生活,在那里每天吃饭睡觉、上班工作、种地放羊、谈情说爱、生儿育女……这种日常性才更为真实,才是不可颠覆的。这种不可颠覆,就像天山、昆仑不可颠覆一样。
关于新疆,我曾有过几个表述,譬如“一席自然的、风情的、文明的盛宴”、“美的自治区”、“以天山为书脊打开的一册经典”、“大地的原典和心经”……我不知道,这些表述是不是好一点,我是一直在不停地修正自己的表达的,能不能接近准确和完美,与我认知的变化和深入程度有关。我想,对于新疆的表达应该是每一个描述者、写作者都应该去逐渐深化的。
汉语的象形很有意思,好像“畺”和“疆”是为新疆专造的一样:三山两盆,持弓守土。何为新疆?新疆是西:西域、西极、西陲、西部、西疆。对于中国古人来说,西是天边的事情、远方的事情。而对于佛教徒,西是西方极乐世界,是天上的事情。《易经》上说:西从金、从泽,金生水,水生木,木生土……这个土就是我们祖国珍贵的疆土。《易经》上还说,西从秋、从羊、从口,分别指的是西部的肃杀性、游牧与漂泊以及歌咏般的感性色彩。下面是我去年写的短诗《疆》:
住在弓上/住在土里/住在高山和盆地//大隐隐于疆
持弓守土者/身旁的/疆/丢盔卸甲者/天边的/畺
弓上的月光/土里的流亡/三山两盆的雪和沙//斯人嘘叹/恰在咫尺天涯
写新疆———我的“新疆词典”
有人将《新疆诗章》和《新疆词典》、《新疆盛宴———亚洲腹地自助之旅》称为我的跨文体“新疆三部曲”。
我主要谈谈《新疆词典》。这本书写了10年。去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增订版,与2005年的旧版相比,变化很大,淘汰了原书的1/3,补写了40多篇,形成了现在的111个有关新疆的“词条”。
运用词典式的写作描写新疆,我应该是第一位。近年我对词典式写作很感兴趣。1990年代初,我读到美国作家安比罗斯·比尔斯的《魔鬼词典》时,很受启发,就有了写“词典式散文”的愿望。为什么用词典体散文来写新疆呢?因为一方面它容纳性大,形式杂糅,文体交错,具备多重视角,有助于呈现新疆的广博与深厚、丰富与多元;另一方面,它的互文性和跨文体色彩,接近我诗歌中所追求的“综合抒情”和“混血之诗”,能把现代学科中的“超文本”概念有效地引入文学创作领域,是对散文的一次解放。
《新疆词典》涉及新疆的人文、历史、地理、人物、动植物等广泛的领域,并将散文、随笔、札记、童话、日记、书信、传记、剧本、散文诗、传奇故事、田野调查、微叙事等10多种文体纳入其中。旧版采用的是主观排序,增订版采用汉语拼音的英文排序,如A下面的“阿拜”等,B下面的“巴扎”等,C下面的“尘埃”等,编排更清晰,更像一本“词典”,便于读者查找、随性阅读。你可以挑感兴趣的词条先看,也可以翻到哪儿就看到哪儿,可以从前往后看,也可以从后往前看,是一种开放式的阅读。
《新疆词典》是一部开放式的“词典”,100个读者可以有100种读法。有朋友说《新疆词典》是“一本可以无限写下去的书”。我现在就在构思,以后希望写一部纯虚构的《新疆词典》,就像卡尔维诺《隐形城市》那种写法,或者写一部讲故事的《新疆词典》,类似《一千零一夜》那样。这样一来,“新疆词典”就有了继续写下去的各种可能。
《新疆词典》是我立体、多角度表达新疆的一次努力,用文学为热爱的土地“去蔽”,还原真实的新疆,从而探索“亚洲腹地的精神地理”。我理解的“亚洲腹地的精神地理”,可以概括为“正午精神”、“正午气质”。为什么叫“正午”呢?这有点西方美学的意味儿,因为新疆位于古地中海(特提斯海)的边缘,在消失的特提斯海边,西与东、近与远、过去与未来,都在这里融汇成了一个整体,是一种西方美学中的“正午”的存在。
《新疆词典》出版时没有前言后记,后来我用诗的方式补写了一个:
“世界的存在是为了成就一本书”/她愿意成为我的一本书吗?/因为她已是大地的心经和原典———前言
我找到爱她的111个理由/同时得到166万平方公里的忧伤———后记
颂扬与捍卫
有人曾问我:“你写诗可能会多一些使命感在里面吗?”“使命感”这个词大了一点,我实际上是带着点忧虑。这种内地新疆人的忧虑跟普通人的忧虑有相通之处,因为它是现代人的“通病”。即便如此,我仍然坚持不要过度忧虑。你焦虑,就会把一个负能量传递给他人。尤其不要为孩子和老人焦虑,要为他们祝福,有一颗祝福之心,把一种好的东西传递给他人。我认为,在我们的写作中,仅仅“以忧解忧”是不够的,写作者要超越焦虑、忧虑,去祝福、祈祷。
有人理解我实际是在追求一种“美的东西”,是的,但我想说,除了美,还有至高的真和善,美与真和善应该同时存在。最近,有一位南疆的画家朋友给我看了一幅他旨在表现反恐的画作,画面很阴郁,恐怖,很令人震撼。我看后感到不安。在给他的邮件中,我说,“直接与恶对应的善,远非高层次的善。”当你直接用狰狞来反对另一种狰狞的时候,势必降低和消解了内心的真和善。艺术就是如此。例如,有的诗人把诗歌作品变成了“个人病例”,这是不值得提倡的。当然,我不是在批评有的诗人,但他们真把诗写成病历了——诗歌体的病历。我不欣赏这个做法,我希望诗是真的善的,同时更是美的。当我表现新疆的时候,这就是我的审美原则。
在新疆生活,我总有一个“梦”,梦想自己成为古代西域三十六国随便哪个小国的一名诗人。每当沉浸在这个“梦”里的时候,就是我更愿面对置身其中的现实——地域、时代、对潮流的旁观、感受个人命运与他人命运的切身性和同一性的时候。这就是文学、诗歌给人的力量吧!是的,这样一种力量,能改善我们的内心,抵御种种野蛮裹挟,免于心灵碎片化、齑粉化。因为我们需要有这样一种力量更加有力地说出“是”。
□相关链接
《新疆词典》是沈苇的散文代表作,该书以“词典写作”的手法,立体、全面地呈现了心中真实的新疆。散文家蒋蓝评价说:“《新疆词典》不但是一部诗性人文之书,也是关于新疆后现代叙事的《山海经》,更是一部凸显新疆的精神史。”
在“阿凡提词条”中作者写道:“阿凡提坐在院子葡萄树下胡思乱想,将一块咬不动的干馕泡进茶水中。这是太阳很好的一天,空气中飘浮着呛人的尘埃,还有令人头晕的沙枣花香。他的伙伴,那头著名的毛驴,正在享用一小堆嫩绿的苜蓿,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看来对自己的现状比较满意。”
在“额尔齐斯河词条”中作者写道:“如果说泥沙俱下的塔里木河是一匹脱缰的野马,奔腾的伊犁河是一条狂舞的游蛇,北方的额尔齐斯河是一位行走的智者。在高纬度的辽阔大地上,它走过了北疆草原、阿尔泰群山和西伯利亚荒原,然后一头扎进北冰洋。它走得很慢,有时停下来,似乎陷入了沉思。……它懂得节约自己的体力,知道‘快’的有害———它用‘慢’来品味和占有时间。”
在“馕词条”中作者写道:“维吾尔谚语说:‘异国他乡的一只烤全羊,还不如故乡的一个热馕。’维吾尔人出门闯世界时,身边总带着馕。他们把馕带到了北京、上海、广州,带到了国外,走得再远,心里也是踏实的。馕就是一个随身携带的故乡,散发着家乡大地、阳光和麦田醉人的香味。”
……
该书抒发着作者对新疆这片土地和人文的深情与热爱。
编辑:邢贺扬
关键词:沈苇 《新疆词典》 新疆 丝绸之路 少数民族 风土人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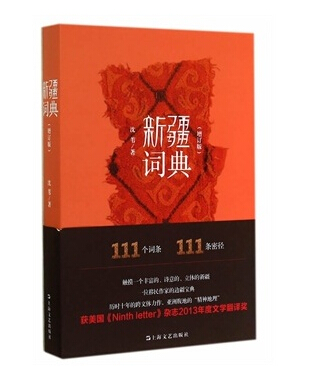


 贵阳机场冬日为客机除冰 保证飞行安全
贵阳机场冬日为客机除冰 保证飞行安全 保加利亚古城欢庆“中国年”
保加利亚古城欢庆“中国年” 河北塞罕坝出现日晕景观
河北塞罕坝出现日晕景观 尼尼斯托高票连任芬兰总统
尼尼斯托高票连任芬兰总统 第30届非盟首脑会议在埃塞俄比亚开幕
第30届非盟首脑会议在埃塞俄比亚开幕 保加利亚举办国际面具节
保加利亚举办国际面具节 叙政府代表表示反对由美国等五国提出的和解方案
叙政府代表表示反对由美国等五国提出的和解方案 洪都拉斯首位连任总统宣誓就职
洪都拉斯首位连任总统宣誓就职
 法蒂玛·马合木提
法蒂玛·马合木提 王召明
王召明 王霞
王霞 辜胜阻
辜胜阻 聂震宁
聂震宁 钱学明
钱学明 孟青录
孟青录 郭晋云
郭晋云 许进
许进 李健
李健 覺醒法師
覺醒法師 吕凤鼎
吕凤鼎 贺铿
贺铿 金曼
金曼 黄维义
黄维义 关牧村
关牧村 陈华
陈华 陈景秋
陈景秋 秦百兰
秦百兰 张自立
张自立 郭松海
郭松海 李兰
李兰 房兴耀
房兴耀 池慧
池慧 柳斌杰
柳斌杰 曹义孙
曹义孙 毛新宇
毛新宇 詹国枢
詹国枢 朱永新
朱永新 张晓梅
张晓梅 焦加良
焦加良 张连起
张连起 龙墨
龙墨 王名
王名 何水法
何水法 李延生
李延生 巩汉林
巩汉林 李胜素
李胜素 施杰
施杰 王亚非
王亚非 艾克拜尔·米吉提
艾克拜尔·米吉提 姚爱兴
姚爱兴 贾宝兰
贾宝兰 谢卫
谢卫 汤素兰
汤素兰 黄信阳
黄信阳 张其成
张其成 潘鲁生
潘鲁生 冯丹藜
冯丹藜 艾克拜尔·米吉提
艾克拜尔·米吉提 袁熙坤
袁熙坤 毛新宇
毛新宇 学诚法师
学诚法师 宗立成
宗立成 梁凤仪
梁凤仪 施 杰
施 杰 张晓梅
张晓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