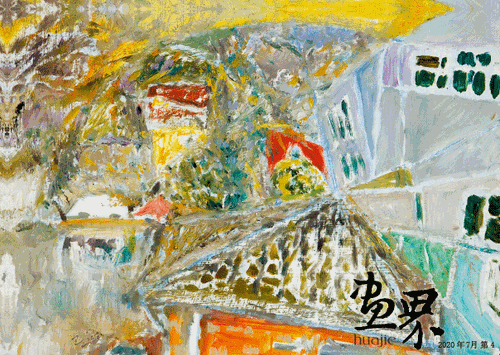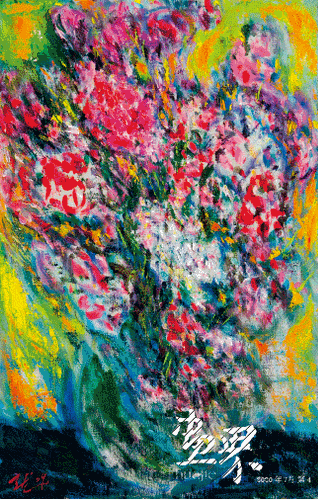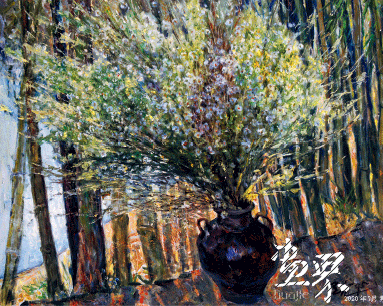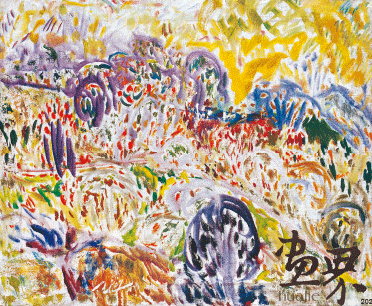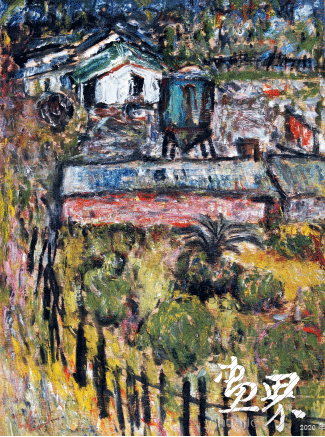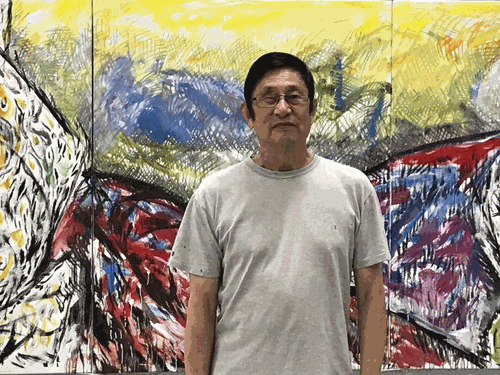首页>书画>画界杂志>2020年第四期
放怀心象孤往者 天真烂漫老顽童
——我看陈天龙绘画
沙尘天(纸面油画)38.2×53cm-2010年-陈天龙
花之二(布面油画)42×27cm-2009年-陈天龙
竹旁瓶花(布面油画)53×65cm-1995年-陈天龙
二十世纪的中国,破帝制,历民国,建共和,归途于改革开放,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美术,作为民族文化的代表,播扬着时代的音讯,传诵着民心的呐喊。油画这一源自西方的艺术,在见证了历史宏大变迁的同时,通过民族救亡和文化启蒙的磨砺,自我陶冶为东方新兴文化的血肉身躯,谱写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创造性转换与生态活化的生动篇章。油画在东方活化的漫长进程中,总有一些生动的片断,深入而直接地镌刻了民族的精神脸谱,在当时和后来,总让人们不断地由此追踪某些意味深长的文化变像。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北京中央美院举办的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讲习班与六十年代初期在杭州浙江美院举办的罗马尼亚专家博巴讲习班,正是这样的珍贵文化片断。两个讲习班风格迥异,她们所代表的不同文化理念,甚至举办院校的先后分布,均成为文化史不断考察、还原追探的命题。时至今日,作为那段历史的当事人,当年的学员们的道路追求、历史命运,仍受美术史界和教育界的格外关注和深化比较。他们的一生都与讲习班无法脱离。“群必求同”,他们总是被作为某种符号、某类群体抛却在二十世纪的美术天幕上。而事实上,他们的艺术追求也确然地受到这道印记根深蒂固的镌刻,代表着这种文化西来变迁的历史命运的共像。无论人生多么坎坷,追求即归踪,命运即家园。
陈天龙先生无疑是当年浙美博巴讲习班中用心最深、命运最为多舛的一个。在其自传中,陈天龙先生谈到,他少时绘画喜在绿叶丛中点上赭色,这其实就是一种挑战与叛逆的青春隐喻。陈先生还深情回忆少年时看表哥在父亲病榻前庄重而冷静地作像。这种“向死而生”的艺术启蒙,不是人人都可能遇到。仅此两例,已然生动预示了这位不断被命运推来搡去的艺者所必将领受的挣扎与命运。进美院就爱上俄罗斯十九世纪的诗性文化,后来又倾心法国十九世纪之后的绘画,最后遇上了埃乌金·博巴,他明白了艺术创造的两个基本律理:一、“艺术应显现个性化的自由”;二、“吸取本民族文化养料以飨油画,让其有新的闪光点”(陈天龙《自述》)。纵观陈先生谈艺,总有一份放怀的顽童快意、高扬艺术表现的烂漫,翔游在自由挥洒的世界中。他将画者表现自我、不被物象束缚称作:“有如鸡虽是蛋中生,而鸡非蛋。”他呼喊:“别把画笔圈在笼子里打转”,“无趣味的画犹如一具本然美人。”这些画家式的自白,狂狷而生动,姿肆而精彩,让人感受到陈先生的脉动,他的不屈追求的心跳。那是非要到独辟蹊径、孤守困顿的深处才可能有的领悟。也是因为这种天性,使他能够抵御命运的种种打击,置身山野,放怀界外,于孤独中坚守追求,于逆境中坚守理想。这不仅使疾病低头,而且也让他在艺术和人生的困境中自寻其乐,以至在耄耋之年,艺术上还酿造出持续的飞跃和提升。
手捧陈先生的这本画集(《陈天龙画册》),我心中颇感震惊。事实上,新千年伊始,我策划举办“金秋放怀”画展时,与陈先生有过接触。那是一个向一代师者致敬的展览。但那之后,在新世纪的短短十年间,陈先生焕发新生,迎来了创造的丰硕金秋。这本画册半数以上的作品创作于这位艺者的耄耋之年,那些生机勃发、精神洒脱的无拘新作,均出自这位往昔师者的衰年变法,这让人震撼不已。阅览本画集的前两部分,第一部分受着岁月与苏派的塑造,第二部分则是那个开放年代的生动写照。敏感求新的中国油画人,几乎将洞开的百年西方绘画史过了一遍。以苏派为主的造型基础和巴黎的绘画变革,这几乎体现了上个世纪中国油画人的两个青春期,对于像陈先生这种年龄段的艺者来说,真正的尴尬是青春期后已临老年。但陈先生的幸运之处在于他所身处的美院的变革传统,在于博巴的教育思想对他潜入骨髓的影响,在于他心神深处的绿叶点赭的反叛与不拘。即便在前两部分中,我们仍可以看到诸般仿学之中深涵着的放手一搏的生命率性;看到的对自由、对民间、对自然弱小生命的朴质关怀;看到受着山水诗性影响并蠢动着的形式趣味。据说,在新世纪将至之际,陈先生遭遇车祸、大难不死,在零下6度作“黄山即景”,隐宿山岙“暮无山居”与大自然结伴作画。于是本画集揭开了第三部分,陈天龙先生仿佛又一次经历置身于死地之后的新生,雨过天晴,放手一搏。
在这里,我有一种揣测。中国美院是由一代大师林风眠、吴大羽等创建。他们几乎都是世纪同代人。新千年到来,美院举办了林风眠、吴大羽系列学术研讨与纪念活动。这些活动不仅拉近了陈先生与林、吴等一代先驱们同为沦落人与独立者的精神联系,而且先师们中国诗性情怀的归宿,也重燃了陈先生心灵深处山水人生的诗性境界。陈先生完全打开,放怀在山居的孤独无拘的生活中,放怀在摆脱具体写景写生、而将山水与心象一例相合相看的自由之中。陈先生仿佛一下子从对象化的风景中跳脱出来,任凭天意,以心作画。《听鸟》的深碧既是林荫又是岁月;《静居水旁》耸立烟雨之中,无限孤单又无限坚强;《窗外街夜》将每日的夜观变作梦魇般的远眺;《稻熟》又将隔岸的观望酿成心情的抒展与变奏。这批绘画,学界称之为中国意象绘画,陈先生自己称之为触景生情的“心象”。“象”在中国文化中原本就是事物与心灵的中介,是将天人合而为一的整体。陈先生借茅屋草舍、离群索居,来归皈自然怀抱,将往昔的执着消解在山寂野处的洒脱之中,让内心与风景融为一体。心因景而体象,景因心而含情。这个情是山水苍然之情,这个象是天人的浑茫之象。如此浓重,又如此放拓;如此俨然,又如此豁然。天人相通,景心相浑。陈先生恍然进入了一个恍兮惚兮的寥廓世界。
2011年.陈天龙先生画了一组山水和《黄日悬空》,被视为中西合璧的经典之作。当我看到这山水中流注着肆意汪洋的滥觞之时,我总是不由地想到中国千古山水诗人们,想到他们在登览传统中的那些宏大视域。欧阳修的《中峰》:“一径林杪出,千岩云下看。烟岚半明灭,落照在峰端。”多少人生的艰辛与逼仄,在此积成一份浑茫的意象,让我们感受到那生命不衰、壮心不已的悲慨情怀。与此同时,我还不禁想到林风眠的苍茫与吴大羽的疏淡。陈天龙先生仿佛阅尽艰辛之后,在自我救赎与抒情放怀的间隙,切近了先师们的观照与知性的底蕴,真正地理解了唐人司空图《诗品》中所弘扬的“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喻彼行健,是谓存雄。”于是我们读到了如地火般烧红了的丘壑;读到了黑云翻墨、白雨跳珠的混茫;读到了谐谑的排雨、丰腻的落霞;读到了西风动草、落日暮云的劲健。《黄日悬空》,陈先生仿佛把我们带到云端,“置身已在烟霞上,还有烟霞最上头”(清·刘源禄《华楼》)。那真正的高天,只在行气如虹的轻轻一抹,返虚而入浑,千古诗人的襟抱,正当目前。
阅读至此,我们跟着这位艺者的放逸之笔行走了很远。经历命运的多舛,经历暮年的山居,经历登览群峦的放怀,经历天真烂漫的顽童洒然,不断地走进了一个自由潇洒的世界,走进一个泰山秋水、向上超越的境界。这个境界,让我想到李白流放夜郎途中,醉游洞庭写下的:“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那敢将洞庭与月色相赊而醉杀洞庭湖的豪情,正来自陈天龙先生一生天真烂漫的顽童之心,以及数十年放怀心象的孤往之志。
(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学院院长)
丽-山(布面油画)50×60.5cm-2007年-陈天龙
院-落(板面油画)61×45.5cm-2002年-陈天龙
山-村(板面油画)48×60cm-2001年-陈天龙
风(布面油画)100×80cm-2009年-陈天龙
陈天龙近照
陈天龙,1935年生于浙江省温州市,1960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原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中国美术学院),1962年毕业于罗马尼亚著名画家埃乌金·博巴(Evgen Popa)教授油画研究生班。1959年赴北京为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绘制朱德油画像及修改十大元帅像。
2006年,在上海美术馆举办《守望自然—陈天龙油画展》,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举办《守望自然—陈天龙油画回顾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心象空间—陈天龙油画展》,2017年,温州肯恩大学建立“陈天龙美术馆”,授予肯恩大学荣誉教授。出版有《陈天龙油画》《守望自然—陈天龙油画作品选》《心象空间—陈天龙》《陈天龙》《一窗之见—陈天龙纸本绘画》《陈天龙水墨作品》。
责任编辑:张月霞
文章来源:《画界》2020年7月第4期“画界人物”
编辑:画界
关键词:先生 天龙 油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