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一代,琴学大兴,甚至引起封建帝王的浓厚兴趣,“宋时置官局制琴,其琴俱有定式,长短大小如一,故曰官琴”(《格古要论》)。宋徽宗本人乃操缦名手,对传世名琴更是汲汲以求,专设“万琴堂”珍藏“南北名琴绝品”,并手绘《听琴图》以名世,蔡京题诗曰:“吟徵调商灶下桐,松间疑有入松风。仰窥低审含情客,以听无弦一弄中”。可见当时朝野上下,无不以能琴为荣,一部迎合最高统治者审美趣味的《洞天清录》也便应时而生。
《洞天清录》封面
唐代古琴大圣遗音(现藏故宫博物院)
听阮图 李 嵩 绘
听阮图 刘彦冲 绘
《洞天清录》的作者赵希鹄,生平事履未详。据明代张萱跋万历刊本《洞天清录》,言其为“宋宗室子”,自幼受高尚生活元素之熏染,“吾辈自有乐地,悦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声……端砚涌严泉,焦桐(古琴的代称)鸣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谓备用清福,孰有愈此者乎”(《洞天清录·序》)。考虑到这样高大上的人生情境并非常人所能想见,“人鲜知之,良可悲也”,不拿出来晒一下简直对不起观众,于是他便将多年来对各类古董珍玩的鉴赏心得与审美经验公之于众,“以贻清修好古尘外之客,名曰《洞天清录》”,列于其首的便是“古琴辨”35条。与中国传统琴学论著偏重于琴曲解题、琴人传略、演奏技法、审美意趣不同,《洞天清录》主要是对古琴材质、斫制方法、形制样式进行品鉴的经验总结,“其援引考证,类皆确凿,固赏鉴家之指南也”(《四库全书总目》)。
唐宋时期,古琴制作工艺取得长足进展,从朱长文所言“四美”——“一曰良质,二曰善斫,三曰妙指,四曰正心”(《琴史·尽美》)不难看出,古琴选材与斫制(良质、善斫)已然超越演奏技法(妙指)和审美意趣(正心),被提到首要地位,无怪赵希鹄感喟:“古材最难得,过于精金美玉,得古材者,命良工旋制之,斯可矣”(《洞天清录·取古材造琴》)。古人在斫琴的实践中发现桐木纹理顺直,性能稳定且不易变形,音色极佳,是制作古琴面板的良材。正如赵希鹄所言,“桐木年久,木液去尽,紫色透里,全无白色,更加细密,万金良材”;“宜择紧实而纹理条条如丝线细密、条达而不邪曲者,此十分良材”。而梓木纹理坚实细密,可以让琴音在槽腹内回旋,取得余音绕梁的共鸣效果,适合用作琴的底板,“今人多择面不择底,纵依法制之,琴亦不清,盖面以取声,底以匮声,底木不坚,声必散逸。法当取五七百年旧梓木,锯开以指甲掐之,坚不可入者方是”(《洞天清录·择琴底》)。对于底面也采用桐木的“纯阳琴”,赵希鹄指出“古无此制,近世为之”,虽然音色古朴浑厚,但共鸣效果不佳,“必不能达远”,非为佳构。
对于古琴面料的选材,赵希鹄将其分为梧桐、花桐(泡桐)、青樱桐、刺桐,“四种之中,当用梧桐”,理由是“梧桐理疏而坚,花桐柔而不坚,则梧桐胜于花桐明矣”(《洞天清录·桐木多等》)。梧桐和泡桐历来都是古琴制作的常用材料,梧桐木质比泡桐密度大,纹理交错,结构粗密,质地坚实,材质较轻,有更好的音响效果。古琴取材都是百年以上的老梧桐,以山石中生长的为佳,但因梧桐不适用于建筑与日常器物,采伐较少,好的琴材极为难得。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梧桐还象征着高洁美好的品格,如“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诗经·卷阿》)、“天资韶雅性,不愧知音识”(戴叔伦《梧桐》);或是忠贞不渝的爱情,如“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孔雀东南飞》)、“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孟郊《烈女操》),正是梧桐这种独特的文化品质,才使其成为琴材的终极之选。
用阴阳理论解释琴材的选择,大约始于北宋《琴书》:“凡制琴,以桐木为阳,楸木为阴”,阴材、阳材分别指琴底和琴面。古琴面料所用桐木按生长方向分为阴阳材,首见于《洞天清录》:“盖桐木面阳日照者为阳,不面日者为阴”。为此,赵希鹄还提供了两种验证方法,一是以水试沉浮;二是在晴天和雨天、清晨和傍晚抚琴以辨别音色。对于后者,赵希鹄还颇为自得,认为“古今琴士所未尝言”(《洞天清录·古琴阴阳材》)。将音乐声学的实践经验纳入阴阳体系加以阐释,在当时并不鲜见,我们只要略一翻检同时代的《梦溪笔谈》之类的科技典籍便可见其端倪。由于日照条件等不同,桐木材质也会存在差异,在音色上存在细微差别,当然是可能的。但居然能随着旦暮、阴晴等环境变化而发生条件反射,甚至“此乃灵物与造化同机,缄非他物比也”,未免耸人听闻。
在制作工艺与藏品选择上上,赵希鹄提出“制琴不当用俗工”“择琴不必泥名”“制琴不必求奇”等原则,对雷氏琴(唐代名琴)、百衲琴等当时推重的“概念琴”颇不以为意,“弹之则与寻常低下琴无异,此何益哉”,主张“依法留心斫之,雷张未必过也,惟求其是而已矣”,对如今泥沙俱下,甚至存在以收藏为名行诈骗之实的收藏品市场而言,倒不失为一针见血的确论。
(作者单位:泰州学院音乐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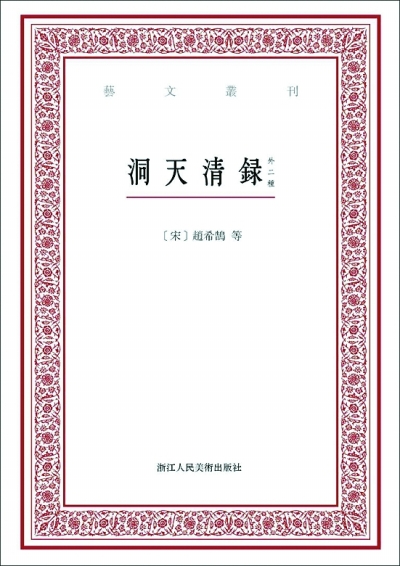





 中国制造助力孟加拉国首条河底隧道项目
中国制造助力孟加拉国首条河底隧道项目 澳大利亚猪肉产业协会官员看好进博会机遇
澳大利亚猪肉产业协会官员看好进博会机遇 联合国官员说叙利亚约117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联合国官员说叙利亚约117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伊朗外长扎里夫宣布辞职
伊朗外长扎里夫宣布辞职 中国南极中山站迎来建站30周年
中国南极中山站迎来建站30周年 联合国特使赴也门斡旋荷台达撤军事宜
联合国特使赴也门斡旋荷台达撤军事宜 以色列前能源部长因从事间谍活动被判11年监禁
以色列前能源部长因从事间谍活动被判11年监禁 故宫博物院建院94年来首开夜场举办“灯会”
故宫博物院建院94年来首开夜场举办“灯会”
 法蒂玛·马合木提
法蒂玛·马合木提 王召明
王召明 王霞
王霞 辜胜阻
辜胜阻 聂震宁
聂震宁 钱学明
钱学明 孟青录
孟青录 郭晋云
郭晋云 许进
许进 李健
李健 覺醒法師
覺醒法師 吕凤鼎
吕凤鼎 贺铿
贺铿 金曼
金曼 黄维义
黄维义 关牧村
关牧村 陈华
陈华 陈景秋
陈景秋 秦百兰
秦百兰 张自立
张自立 郭松海
郭松海 李兰
李兰 房兴耀
房兴耀 池慧
池慧 柳斌杰
柳斌杰 曹义孙
曹义孙 毛新宇
毛新宇 詹国枢
詹国枢 朱永新
朱永新 张晓梅
张晓梅 焦加良
焦加良 张连起
张连起 龙墨
龙墨 王名
王名 何水法
何水法 李延生
李延生 巩汉林
巩汉林 李胜素
李胜素 施杰
施杰 王亚非
王亚非 艾克拜尔·米吉提
艾克拜尔·米吉提 姚爱兴
姚爱兴 贾宝兰
贾宝兰 谢卫
谢卫 汤素兰
汤素兰 黄信阳
黄信阳 张其成
张其成 潘鲁生
潘鲁生 冯丹藜
冯丹藜 艾克拜尔·米吉提
艾克拜尔·米吉提 袁熙坤
袁熙坤 毛新宇
毛新宇 学诚法师
学诚法师 宗立成
宗立成 梁凤仪
梁凤仪 施 杰
施 杰 张晓梅
张晓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