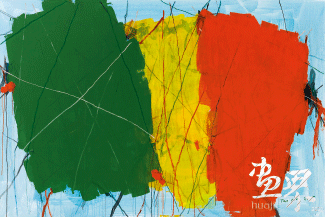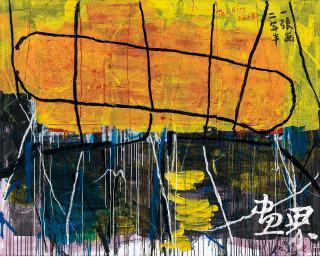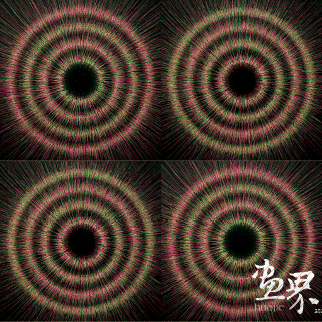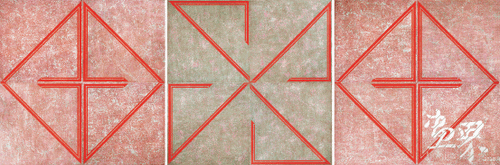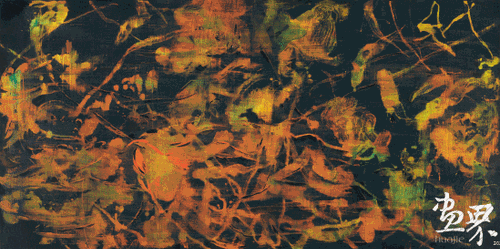首页>书画>画界杂志>2020年第四期
秩序向—谭平、孟禄丁、顾黎明、陈思源的抽象艺术
“在艺术中须有一种秩序,也就是一种共同的东西,四位艺术家其实内在的文化气质上是一致的,都是用抽象性的艺术语言方式,判断和确定当下艺术诉求的多方位、多视角、多层次的艺术探索状态,借助共同的语言方式,试图重新深化一种更趋自己的社会文化形态化的艺术探索方向。”— 顾黎明
再论谭平
易 英/文
谭平有非常优秀的艺术感觉,也就是一个画家在形式上的独特感受性,别人感受不到的东西,他都能敏锐地感觉出来。上学的时候,我在壁画系的走廊里看到他的水粉画—静物和人体,就觉得他画得特别好,颜色和形式都有自己独特的处理,不是那种油画的调子,有点装饰性,但是很写实。那时我就想认识他,跟他学两笔。
如果他没有去德国留学的话,他会不会是一个表现主义画家?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走向完全的抽象?出国之前,他画略带表现性的都市题材。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的都市题材表现就是很超前的了。他关注人和都市的关系,人在都市的处境,特别是精神的困境。他对题材不是特别感兴趣,不会去深挖作品的主题,并且他透过形式琢磨出的抽象认识不是来自某种规则和价值,而是来自自身的体验,任何再现的道理和抽象的原则,都不足以实现他那种无人能企及的感受性。
谭平的抽象首先是对现实与表现的跨越,这也是基于他的内在需求,他的超常的形式感召力。但他完成这个跨越之后,怎样进一步发展就成了问题。对他来说,基本上有两种选择。一个是精神的介入,让抽象的形式具有生命的意义。记号在谭平的抽象画中有重要作用,或者作为构成的要素,或者作为精神的符号。谭平在这方面不是很明确,虽然达到了很好的效果。他一度把记号解释为生命的某个阶段的精神记录,但是这有特定的时间规定性,一旦某个事件的精神影响在生活中淡化,这个记号将不再有精神的力量,甚至导致图式的无意义重复。谭平最近的抽象素描就有这种可能性,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心境,产生特定的心理图式,这一定要有外部的压力,但我们不可能期待源源不断的外部压力。重要的是第二种选择,继续推进抽象的表现,这是谭平艺术的本质所在。就他的作品来看,这是一个转折点。从一个更大的范围来看,这也是中国当代的艺术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架上绘画而言,面临着一种困境,一种突破。谭平在这方面,以个人的实践为基础,尽了很大的努力。
2000年以后,中国的当代艺术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多种可能性,尤其在材料语言、视觉形态上。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和发展,以及大众文化的泛滥和艺术市场的兴起,架上艺术逐渐失去了以前的主流地位,抽象艺术也深受影响。抽象艺术是很难商业化的,抽象艺术的展览难做,就在于赞助商不收抽象画,不是他们不喜欢抽象,而是觉得没有商业价值。市场的旁落可能更有利于艺术的思考和纯粹,抽象艺术在当代艺术的角落里面更显现出独特的价值。前些年,正好有一个展览,李向明和尚扬老师都参加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抽象上采用了一些材料,一些有限的现成品。这反映出抽象作为一种纯粹的视觉表达,从传统绘画到现代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商业社会、消费社会所提供的视觉资源之间的转换,从抽象表现转换到极少主义的时候不会转回到绘画本身,而是转换到装置、影像。实际上整个绘画开始出现边缘化的倾向,尽管市场很热闹。这样抽象就更加边缘化,因为和它的前两个阶段—比如说后古典阶段和工业化阶段—那样丰富的资源相比,它的资源非常有限,因为后现代的资源大部分是被直接使用的新的材料所取代,那么抽象艺术,我们把它叫作后抽象,它的可能性是什么?这就是谭平要探索的,它已经不可能在原来从绘画发展过来的抽象,从传统、从古典发展过来的抽象这条路上走了。因为它的资源已耗竭,得添加材料、现成品的材料。
谭平在这里抱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不管别人怎么看,继续推进自己的抽象艺术,而且他在骨子里认为这个东西是最好的。他不会跟我争辩:艺术要不要转型?架上艺术有没有前途?他仍然在推进自己的“感觉”抽象,探求能否把自己那种独一无二的形式感受挖掘出来。但是,他还是改变了策略,使他的抽象有了全新的变化,但仍然在框架内。不能说他的方式是前无古人,但还是有他的原创性,可以将他的新搞法放在“过程艺术”里面,过程并不是目的,过程实现的还是传统的抽象,没有综合材料或平面装置,有的是更深入的感觉挖掘。
可能是由于工作的原因,谭平的创作时间非常有限,很难有较长的时间对画面进行经营和思考。他的作品是分几次完成的,每一次作业都是对前面的覆盖,没有小稿和草图,也没有既定的程序安排,在时间的紧迫中终止于偶然的效果,这个偶然效果可能也是潜意识中预设的方案。“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就是在无意识的行为过程中实现意想不到的效果。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如德·库宁和罗斯科,都采用过覆盖性作画的方式,一遍一遍地涂抹颜色,或者是达到偶然的效果,或者是强调过程的意义。谭平的覆盖有观念的性质,但更重要的还是形式的创造,即抽象的表现或视觉的纯粹。
覆盖是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不是行为艺术的过程,也不是表演的要求,尽管他有些作品有表演的性质,如用视频记录他作画的过程,图像的不断抹擦和重构确实有表演的成分。在这方面,他倒是有些接近波洛克的“泼洒”作画,波洛克说形式有其自己的生命,艺术家的工作就是在行动的过程中,让形式自动显现出来。在波洛克那儿,形式显现为最终的结果。谭平与此不同,每一个“过程”都是通向结果的一个阶段,每一次覆盖都是在探索一种新图式的可能性,也是对极限的检测。
谭平的抽象画越来越大,大画为覆盖的可能性留有更大的空间。谭平说画大画是一种能力,因为小画好控制,大画难控制,创作大画的每个过程都是面对一个局部,在处理这个局部的时候,要想到那个局部。在有形式的地方要想到没形式的地方,这是一种无形的控制。我们现在看到的谭平的画,不论是复杂的图式还是极简的单色,不管是痕迹、记号还是符号或构成,甚至那种把线条做到极致的搞法,都是多次复合的产物,是一个不断破坏和重构的过程。
还要补充一点,最近看了谭平的新作,好像没有那么多的覆盖,主要是一次完成的抽象表现,强烈的颜色对比,复杂与极简的交错,富于手感的线条,洋溢着乐观的生命力。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覆盖的结果,就像我们的长途旅行一样,翻越大山之后,总会遇到一个盆地或平原,一片美丽富饶的景象,然后又会进入大山。
(文章有删节,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无-题(布面丙烯)120×120cm-2018年-谭平
无-题(布面丙烯)120×150cm-2014年-谭平
禁-行(布面丙烯)200×300cm-2015年-谭平
无-题(布面丙烯)200×300cm-2018年-谭平
一张画两年半(布面丙烯)160×200cm--谭平
不要被他随性的外表迷惑—论孟禄丁
张晓凌/文
孟禄丁这个个案确实比较独特,首先独特在少年成名,他在大二的时候就画了《在新时代—亚当夏娃的启示》,这张画影响很大,可以说是“新潮美术运动”的标志。当时大家都觉得很新鲜,因为中国人的视觉经验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中就是“写实主义”,“写实主义”就是尊重焦点透视,在一个人的视野范围内表达主题,你不能超越这个范围。孟禄丁突然采用了一种超现实、超视觉的方法来表达冲破禁区这样一个主题,一下子激起了美术界、乃至整个社会要求改革的人们的共鸣。孟禄丁以一个学生的身份敏锐地捕捉到了改革开放年代人们的一种精神诉求,所以说他少年即成名。这件作品在社会上引起很大轰动,我看现在很多人写艺术史都要把这幅画写进去,就是说孟禄丁最初的创作就具有艺术史价值,这是了不得的。
第二个独特的方面,就是“新潮美术运动”起来以后,本来是沿着语言本体推进的,结果跑着跑着就进入了功利主义阶段,也就是说我们搞新潮美术的目的不是为了艺术,而是为了思想启蒙,是为了给整个改革提供一种图像背景。比如栗宪庭一直主张“重要的不是艺术”,这样一来,政治就成为艺术的一个主要主题。如果政治是艺术的主题的话,那艺术又在哪里?我记得好像是在1986年后期,孟禄丁就开始质疑了,他从新潮美术的发动者变成了怀疑者:艺术难道永远做政治的工具?做思想启蒙的工具?他认为艺术不止于此,艺术有它自身的价值,即语言、形式、色彩,线条等有独立于政治以外的超越性价值。所以他写了《纯化语言》的文章,开始反对当时的动向,要把艺术从政治的战车上解脱出来。但在那样一个大的形势下,孟禄丁的声音相对于整个“新潮美术”浪潮来说还是比较微弱的,不过这个声音显得非常清澈。
这两件事就证明孟禄丁在二十几岁的年纪就担当起了新潮美术的推动者、怀疑者这样的角色,有意思的是,这个角色的前后还是矛盾的。他在《在新时代—亚当夏娃的启示》以后,类似的作品就很少了,紧接着转向了抽象艺术,强调艺术的相对独立性。紧接着他就出国了。当他去德国、美国转了一圈回来以后,画风有比较大的变化,对此各种解释都有,我认为可能更多地指向了他的本心。就是说过去可能更多的是考虑一些社会问题和时代诉求,把绘画弄得太复杂了。回国以后他用机器作画,就是要把艺术纯化,对物质、生命、艺术本体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即“物自体”包括颜料、画布和机器之间构成了一套自在自为的生命体系,其运动的结果是你根本无法想象的。
你别看孟禄丁平时嘻嘻哈哈的,实际上他比较喜欢读书。在同代人中,他是悟性绝佳的一个,这是上天赋予的。孟禄丁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他这个人不动声色地就转换了自己的语言,他每次转换都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标志,自然而然就转换了,等你发现,他已经转得非常棒了。比如他的新作“朱砂”系列,我也是刚刚了解到。我跟孟禄丁说过,回归母体是所有民族的成名艺术家的一个标准。每一个人,不管你如何千变万化,你了解多少国家的语言、文化、艺术,最根本的,就是你的手、脚是不是紧紧地抱住你的母亲的土地。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为了有一天要更好地回归母体,在这里才能获得真正的资源。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孟禄丁从出国到回归,从“新潮美术运动”的奠基者到怀疑论者,再到本土现代文化的建构者,这几个大的变化已经奠定了他在艺术史上一个基本的地位。事实上,他在艺术史上的地位远比现在很多卖得好的艺术家要高。
孟禄丁是个清醒者,他的内心是严肃的,他对艺术史、对文化的发展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不要被他随性的外表迷惑,他内在的情怀是个真正有风骨的中国知识分子,他有启蒙情结,有英雄情结,有救赎情结。不是只为个人利益,而是以天下为己任。
(作者系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美术评论家)
元-速(布面丙烯)200×200cm×4-2013年-孟禄丁
朱-砂(黄麻、矿物质颜料)145×12cm-2019年-孟禄丁
山水赋
顾黎明/文
我们人类经历了三种观看方式,一是祭祀、宗教性的观看,二是人的自我审视观看(此在),三是图像化的观看。两千多年前的汉代画像石所绘的三种场景:一为地狱的炼狱,二为人世间的日常,三为升天后的另一个世界。天堂里的这个世界不是罗丹地狱之门顶端上的上帝,而是以自然动物朱雀、玄武和青龙、白虎的替化,使人性终极转化为自然的化身。这是人对生命的终极期许,也是人对自然的归属。而在今天这个科技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传统的人与自然的秩序体系却逐渐被淡忘,甚至是摈弃,人们对自然的灵性感知基本退化。这是人类的遗憾,也是人类的悲哀!
其实,至今为止,我们的观看仍停滞在两个界地,即自然凝练的秩序和图像化的移植,前者是语言化的技术层面,后者是无深度的“他者”视域。我们很难再从自然的秩序中来框定自我知性。所以,如何在科技化、信息化和人性化的当下社会,构建另一个人与自然契合的心迹世界,以反观我们所处的尴尬境地,是揭示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空间的重要因素。
观看是一种态度,观看是一种反思。
其实,我们已不再生活在现代主义的英雄主义时代,个人自我救赎的语言方式很难表达科技信息时代的变迁,我们的观看受制于图像信息化的诱惑,虚拟的现实性左右我们的生存空间,乃至价值判断,导致我们很难辨析这个被虚拟包围的现代世界的真假。同样,我们也回不去古人那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相融的境地。由此,在我对自己的质疑过程中,唯有呈现这种纠结的状态印记才是真实的感受。这种印记应该是裹挟前人的历史图式,现实的冲突感受及图像化时代所带给我们的视觉单一甚至是苍白。
虽然这个时代科学技术与消费文化无边界地统领着发达的人类社会,总以为信息图像化时代只是更利于自我发展的便利手段,所以,由图像到图像的欢娱互动成为一代代无穷无尽的游戏体验。于是,观看也在脱离以自然为参照的审视和凝视,在游戏化、戏谑性的虚构的“真实”中坦然呈现。
观看的本质是面对真实凝练自我,而图像信息化的真实却是借助他人的眼睛的“真实”。所以,我们当代人的真实是借助“他者”的呈现,也就没有了自然为本的心性的价值判断。
我的《山水赋》系列不是对真山真水的观看,也不是寻觅远逝的山水境地,更不是体味视觉的饕餮,而是探索传统的山水秩序在今天所遭遇的问题。试图效仿前人的对山水掌控的艺术要素,借助多重的媒介材质,通过“触感”的痕迹,表达我自己在当代语境下与前人对自然认识的差异与冲突,呈现当下人的心理状态。“触感”不仅是对陌生事物的身体性感觉,也是人在世界中的身体性存在的方式。我通过仿效与追忆,在前人的历史文化状态与现实的在场冲突中,试图重构一个现代与传统、人与自然相互冲突的当代山水境遇,引人反思。
科技化、信息化、经济一体化的社会,让国与国、人与人连在了一起,给我们的生存带来了太多的便利,但我们失去了对事物认知与把握的鲜活性,没有了人对自然依存的秩序感。前人对山水的感悟,恰恰使我们反观当下人性的缺失。实际上,世界发展到今天,不是谁离不开谁的问题,而是我们人类重新审视自己建立起来的这个现代化的世界秩序有多少与休戚相关的自然相宜共生。
当“COVID-19”疫情肆虐欧洲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呼吁的“例外”又一次让我们深度感受到暂时彼此的隔离所潜伏的社会危机,而拆除这一道道不断困绕我们的藩篱,唯有人在自然的境遇里反观自己,才会让“例外”消解在人与自然的秩序和谐之中。
借用2018年我为思源写过一篇文章的最后一段文字为启示吧:“不傲睨于万物”但又是难以企及的久远。在科技化的信息时代里,人类又能如何掌控、平衡未来的世界?是否我们今天还有资格去得到精神与天地相通的境地?(文章有删节)
枯山水-395×146cm-2003-2016年-顾黎明
山水赋之二十二(卡纸上色粉笔、水彩、铅笔及蜡纸拼贴等)150×93cm-2015年-顾黎明
山水赋-鹊华秋色NO2(卡纸上色粉、丙烯水彩及拼贴等)156×107cm-2019年-顾黎明
山水赋NO21(卡纸上色粉、水彩、铅笔及蜡纸拼贴等)75×46.5cm-2016年-顾黎明
陈思源的新绘画:斑斓的余象
夏可君/文
当前中国艺术的创造力在于回到自身文化根源性的想象力才可能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与感知方式。何谓此根源性的想象力?这是中国人原初面对世界的诗性感受:面对世界的变化无常,以蒙蒙如烟然的流动形式来回应此无常变化,还能够赋予此变化以诗性的韵律,既要达到即刻幻化,又要透明如镜,激活自然之新的可塑性,并且具有诗意的余味,面对现代性的无根状态,生成出新的余象。
作为一个酷爱诗歌的画家,陈思源这些年一直试图通过此诗意的感受来重新打开绘画,与一系列诗人的密切交往与对话,让他不断寻找着化解物象与颜料的方法,使之释放出诗意的氛围,让自然的灵氛与灵晕再次来临。他内在地认识到,只有重新激活中国文化特有的可塑性活力,这既是自然元素的可塑性,也是颜料质感的可塑性,以水性的元素性化解油性的粘滞,并且重建一种诗意的灵氛,才可能让新绘画发生。
当代绘画有待于回到个体手感与时代生存经验,诗歌可以最好地经验到个体生存的现代性感受,这就是无根的漂浮感,离开了此虚无的拔根感受,如何可能有现代性艺术?中国当代艺术家之所以在绘画语言上没有原创的贡献,就在于绘画语言不是从生命感觉上生成出来,或者无法赋予此感受以诗意的根源性塑造。面对此无根状态,更为不确定的变化无常,如何以艺术语言来塑造之,并获得新的形象与形式语言?陈思源与诗人们的交往,加强了这种现代性感受的自觉。
如何让生存经验及其表达的困难在绘画上重新生成?陈思源在画布上苦苦挣扎,直到撕碎各种已有的目光,在混杂而无序之中,让色彩在幻化之中飘舞起来,在一个奇妙的瞬间,他似乎看到这些色片就是柳絮,世界最为基本的元素就是这些漂浮着的无根的柳絮,近天命之年的艺术家为何突然敏感于这秋日飘飞的柳絮呢?为何对无根飘散的柳絮状物如此着迷?这是因为此絮状之物触发了一个严峻的时刻,一种悖论的经验:这既是秋日之成熟,一切已经干透,还带有果实的饱满;但另一方面,此柳絮从枝条分离而在空中飞舞飘动,处于无根状态;一种现代性的生存诗意感受,也正是一种中年的诗意—果实累累又瑟瑟秋风,一种逆觉发生的时刻,絮意与絮感—这是秋天的诗意粮食,在诗意幻化的目光中获得色彩与形式。
如何达到此诗意的幻化并在平面上打开透明的深度?陈思源就是一遍遍地画,一遍遍再擦洗掉,反复擦掉留下的残痕,使之具有多向性与不确定。而在空间层次上,彼此分离的柳絮或者色彩,在流动中建构不确定的物象,纯粹从色彩的对比度与空间层次来建构画面,并且通过颜料的化解,让色彩透明,空间透明,并不陷入抽象的重复,而是让漂浮的斑斓色彩,反复地交织与交错,打开了内部的呼吸与透明空间,并且在画面上营造出一种朦胧的诗意氛围。
画面本身在反复涂擦之后,还依然保留了一种薄透感,光感的透明度,似乎如同水彩,带来烟岚之气,又有着薄膜的通透。这些絮状物在漂浮着,又如同水墨罩染一般,画家以水墨的呼吸性来化解颜料的粘滞感。画家在营造画面深度空间时,为了让画面透明的透气感不被堵塞,经常会停顿下来,观察很久,几乎不敢画,即让每一层笔触都留下来了,又保持其模糊的过渡性,瞬间的触发性,相互的呼应,每一片色彩,斑斓而炽烈,画面在激烈的燃烧中,还保持层层的透明,一次次的重叠,又依然薄如蝶翼,打开平面上的虚厚感。
绚烂的色彩在画面上隐含书写性的线条,但一切处于化解与过渡之中,相互的召唤与呼应之中,色彩终于触动了空气与阳光,如同蝴蝶的翅膀在颤动中感应世界的细微变化,因此绘画并不仅仅是色彩关系,而是让色斑在不确定中相互寻找,这是飘浮中的相互吸引,这是万物的隐秘合唱,这是世界的梦絮,是诗意的斑斓,是色彩的颂歌。
绘画的色彩与笔触通过悖论的关系而生成:破坏又重建,塑造又抹去。看似形成某种风景图像,但在色彩的叠加中又被重新想象,自然的可塑性得以强化,局部看起来如同抽象,其实整体上隐含着无数可能的形象。因为反复绘画之后,无数的笔触都余留下来,让画面具有了新的生长因子,又因为拟自然之物,这就让画面生成为一种抽象化的余意,即让每一道笔触都仅仅具有剩余的意味,但在整体上,又生成出一种可能的形象,激发新的联想。
陈思源的绘画纯然依靠色彩与笔触的力量,不断激发诗意的联想,保持可塑的生长性,让笔触在反复涂抹之中,再次重新生成,如此的绘画方法,就重新触动了绘画的平面,一种不断抽象化却又不断接纳自然的虚化,其诗意的余象,让我们再次进入自然的密码,倾听自然隐秘的歌唱。
绘画纯然以色彩的细微差异与过渡,打开一个深度的迷宫式空间,这是充满诗意色彩的迷宫,而且是诗意的深度,绘画得以继续。
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虽然让绘画回到了平面的平面性上,但丧失了自然性与诗性,而通布利试图让涂写再次回到诗性与自然性,但还是过于表现,对于自然的丰富性挖掘不够。中国当代绘画,就是更为丰富地重建此诗意性与自然性,带有抽象的笔触,但又并非抽象画,而是一种余象的触发,是其色彩碎片的斑斓生长。
陈思源每日的绘画,乃是与色彩一道生活,让色彩具有诗意的灵氛,画面上的色彩所打开的空间滋养了每日的辛劳,这是绘画的奖赏。这是绘画所具有的现代意义,它代替了诗意的贫乏,使之更为绚烂。尤其在一个影像复制时代,绘画绚烂而迷人的色彩,可以让我们重新回到生命的感性,面对日常虚无主义的侵袭,只有绘画的诗意与内在的空间,让我们可以抵御现实的伤害。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美术策展人、评论家)
回-声19-2(油画画布)180×180cm-2019年-陈思源
延伸的秘语-No22-3(布面丙烯)150×120cm-2020年-陈思源
回-声-No26-1(布面丙烯)150×120cm-2020年-陈思源
与物容19-3-80×160cm-2019年-陈思源
责任编辑:张月霞
编辑:画界-邢志敏
关键词:艺术 绘画 谭平 孟禄丁 顾黎明 陈思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