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书画·现场>讯息讯息
史景迁:人生之乐乐无穷 繁华靡丽皆成空
自绚烂归于平淡 从国史写到家传
张岱的深邃虚幻 史景迁妙笔重塑
只要有人追忆,往事就不必如烟
史景迁细数张岱心灵点滴
窥探亡国知识分子的内心转折
同时瞥见晚明的精緻生活美学
张岱是明代散文大家,传世名著《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堪称晚明小品文代表。他出身仕宦家庭,早年衣食无忧,品茗、製茶、赏月、弹琴、斗鸡、蹴踘、观雪、狩猎、听戏、吟诗、游湖、收藏、鑑赏,样样精通,生活围绕在读书与享乐间,光鲜快意。清兵入关后,年过五十的张岱遭逢人生重大转折,位于杭州的别墅、绍兴的家园、丰富的书画古玩收藏,悉数毁于战火。「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他带著倖存的家人逸隐于绍兴龙山,馀生力修明史,八十八岁方成《石匮书》,书成后不久亡故。
个人历史与家国历史相互映照、无法切割。不论是怀志一生纂修的明史《石匮书》,还是《陶庵梦忆》裡一幅幅简约、多情善感的前朝旧事,都镶框著家族轶事与大时代的层层跌宕与悲喜交错。张岱一生的浮华与苍凉,在梦与忆的交错摆盪间,隐隐浮现。如何透过回忆与书写,扎实一个捉不回的梦?史景迁说:「他生于、长于龙山山麓,中年归返龙山,只为将心中了然之事理个清楚。……他理解到只要有人追忆,往事就不必如烟,于是他决心尽其所能一点一滴挽回对明朝的回忆。」
张岱对曩昔纨裤生活的点滴追忆,召唤的终究是国破家亡的苍凉与悲愤,以及知识分子在历史巨变下,以书写对抗遗忘的自觉。史景迁书写张岱的一生、内心转折及过往追忆的同时,更探讨张岱身为知识分子,是如何藉由回忆以及修史确立自身的存在价值。在得失之间,唯有捕捉消逝的回忆,以书写对抗遗忘,才能坦然面对、甚或抵抗世事的变迁与生命的无常;这一点,无疑反映了历史与书写的本质与关系。

正文节选
第一章 人生之乐乐无穷
张岱的三叔张炳芳饱历世故,品味精纯。叔姪两人切磋品鑑,百般调配,以各处名泉煮各地名茶,找出最能相配的茶与泉。这对叔姪的结论是:取斑竹庵泉水,放置三宿,最能带出上等茶叶的香气,再注入细白瓷杯,茶色如箨方解,绿粉初匀,举世无双。至于茶叶应否杂入一两片茉莉,叔姪两人对此意见不一,但是两人都认为最好是先将沸水注入壶中少许,待其稍凉,再以沸水注之:看著茶叶舒展,「有如百茎素兰同雪涛并泻也」,叔姪两人遂将此茶戏称为「兰雪」。
张岱总是想尝试各种新奇口味,还钻研各种兰雪茶的饮法。张岱曾养过一头牛,研製做乳酪的方法。张岱取乳之后,静置一夜,等到乳脂分离。以乳汁一斤、兰雪茶四瓯,搀和置于铜壶,久煮至既黏且稠,如「玉液珠胶」。待其凉后,张岱认为其吹气胜兰如「雪腴」,沁入肺腑似「霜腻」。张岱还拿它做更多的尝试:以当地佳酿同入陶甑蒸之,或搀入豆粉发酵,或煎酥,或缚饼,或酒凝,或盐醃。也可用蔗浆霜温火熬之、滤之、钻之、掇之、印模成带骨鲍螺状。无论何种料理妙方,张岱都将烹调祕诀锁密房,「以纸封固,虽父子不轻传之。」
不出五年,也就是约当万曆四十八年(一六二○年),张岱和三叔张炳芳命名的兰雪茶已经甚受名家青睐。但是却有不肖商贾以兰雪之名,在市场上哄售劣质茶,而饮者似乎并不知道。后来,就连斑竹庵禊泉的水源也不保。前有绍兴商人以此泉酿酒,或在泉水旁开茶馆,后又有地方贪官一度封泉,想将泉水据为私有。这反倒让斑竹庵禊泉的声名更大,引来无赖之徒,向庵内僧人讨食物、柴薪,若是不从便咆哮动粗。最后,僧人为了恢复昔日宁静,就把刍秽、腐竹投入泉水,决庵内沟渠以毁泉水。张岱三度携家僕淘洗,僧人也三度在张岱离去又毁泉。张岱最后只好作罢,但说来讽刺,一般人还是难挡「禊泉」的昔日名气,继续以斑竹庵不洁的水来煮茶,还盛讚水质甘冽。
但是,这种事情张岱也看开了,而且他也深谙水源流通之理。他写到另一处清泉时说:「惠水捐捐,繇井之涧,繇涧之谿,繇谿之池、之厨、之福,以涤、以濯、以灌园、以沐浴、以淨溺器,无不惠山泉者。」所以,张岱认为,「福德与罪孽正等。」
张岱愈是发展某种感官,品味也愈是因而改变。张岱既然求好灯,自然也会寻访造灯的巧匠。张岱找到一位福建的雕佛师傅。这位师傅雕工极细,抚台曾请他造灯十架,耗时两年才完成。可惜灯还没造成,抚台就已辞世;当地一名李姓官员也是绍兴人,将灯藏在木椟中,带回绍兴。李某知张岱好灯,便把灯送给张岱。张岱不愿无端受礼,当场就以五十两白银酬谢李某。五十两不是个小数目,但是张岱认为这还不及真正价值的十分之一。在张岱心中,这十座灯成为他收藏的压箱宝。
其他巧匠的作品也充实了张岱的收藏。绍兴匠人夏耳金擅长剪綵为花,再罩以冰纱;张岱大歎巧夺天工,「有烟笼芍药之致」。夏耳金还会用粗铁丝界画规矩,画出各种奇绝图案,再罩以四川锦幔。每年酬神,夏耳金一定会造灯一盏,等到庆典结束之后,常常以张岱所出的「善价」卖给他。张岱还办了龙山灯展,为此向南京巧匠赵士元购灯。赵士元精于造夹纱屏与灯带,当地匠人无人能及。张岱的收藏品日丰,他也发现家中有一小厮很会保养灯,「虽纸灯亦十年不得坏,故灯日富。」
张岱的癖好常常变来变去,难以持久,但是他写到这些癖好时,却彷彿是入迷极深,足以为安身立命的依託。张岱开始尝试各种泡製兰雪茶之后过了两年,他又迷上了琴。万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时年十九的张岱说动了六个心性相投、年纪相近的亲友跟他一同学琴。张岱的说法是,绍兴难求好琴师,如果不常练琴的话,琴艺就无法精进。张岱写了一篇雅致的小檄文,说缔结「丝社」的目的是要社员立约每月三会,这比他们「宁虚芳月」要好得多。若能定期操琴,便能兼顾绍兴琴歌、涧响、松风三者;一旦操练得法,「自令众山皆响」。这些念头常放在心裡,便能「斜畅风神」,而「雅羡心生于手」。
张岱的陈义高蹈,并不是人人能及,张岱的堂弟燕客曾参加丝社,但仍是不通音律。范与兰虽然有兴趣,但是进步仍然有限。范与兰有一阵跟某琴师学琴甚勤,努力得其神韵,后来改投另一琴师门下。没过多久,范与兰尽弃所学,又拜师从头学起,如此复始数次。张岱写道:「旧所学又锐意去之,不复能记忆,究竟终无一字,终日抚琴,但和弦而已。」
张岱认为自己比较高明,拜各家名师学艺,勤加练习而至「练熟还生」,能刻意奏出古拙之音。张岱有时会同琴师一位、琴艺最精的同学两位,四人常在众人前合奏,「如出一手,听者皆服。」
到了天启二年(一六二二年),二十五岁的张岱又迷上斗鸡,与一干同好创斗鸡社。斗鸡的风气在中国至少盛行两千年,早有一套磨练斗狠的祕技。斗鸡通常进行三回合,斗到鸡死方休。据说斗鸡名师能把斗鸡调教得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对声响、阴影无动于衷,临阵对敌不露情绪。上品斗鸡应如机械,教对手望之丧胆却走。文献记载,训练有素的斗鸡「羽竖、翼鼓、嘴尖、爪利、沉著、冷静克敌」。上品斗鸡一看外观便知:羽毛疏目短,头壮且小,眼窝深凹而皮厚。
张岱创丝社写檄文,创斗鸡社也是如此;不过张岱此举已有先例,八世纪的唐代诗人王勃写过斗鸡檄文。张岱的二叔张联芳在古玩、艺术品的收藏很有名,他也是斗鸡社的基本成员。叔姪两人下重注斗鸡,赌金有「古董、书画、文锦、川扇」。根据张岱的记述,张联芳十赌九输,愈输愈恼。最后,张联芳竟然把铁刺绑在斗鸡的爪上,还在翅膀下洒芥末粉――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训练方法,也为斗鸡所容许。樊哙是汉代斗鸡名家,张联芳还派人暗中寻访他的后代,但是并无收穫。后来,张岱知道自己与唐玄宗命盘相同,而唐玄宗好斗鸡又亡其国,于是张岱便以斗鸡不祥为由,结束了斗鸡社,叔姪俩才又和好。
天启三年初,张岱才刚戒了斗鸡,又与弟弟、友人迷上看「蹴踘」(类似足球)。所谓的蹴踘并不是一般的运动比赛,而是一种动作灵巧、身形优雅的技艺形式,玩蹴踘的人必须尽可能让球近身。蹴踘这门技艺也是历史悠久,男女、廷臣、常民都可参与,有时还结合了其他的运动与赌博。张岱这麽描写一位善蹴踘的人,「球著足,浑身旋滚,一似黏疐有胶,提掇有线,穿插有孔者。」
有些技艺非凡的蹴踘玩家,本身也是梨园弟子,张岱家中戏班裡就有几个人是如此,因为张岱也迷上看戏,精研唱腔、身段、扮相。张岱与亲友结成的诗社历时最长。他们定期聚会,就题吟诗,共赏购得的珍稀古玩,想出有典故又妥切的名称。等到这群人对吟诗失了兴味之后,便碰面「合采牌」,但用的不是一般骨牌,而是张岱自己设计的纸牌。纸牌各有名目,是明人生活不可或缺的娱乐,文人武将都很热中。张岱的堂弟燕客学琴虽然不成,但这人却很有想像力,很会设计新牌戏,取类似之牌,从中推陈出各种色彩名目的牌子。
张岱还提到亲友的其他结社:祖父张汝霖立「读史社」,有个叔叔成立「噱社」,张岱的父亲张耀芳喜欢和三五好友,考据旧地名辞源,以地名来想谜题。而张岱自己最喜欢的是「蟹会」,不过他没说是什麽时候创会的。阴曆十月正是河蟹当令,蟹螯色紫且肥,蟹会只在十月的午后聚会。蟹会吃蟹,不加盐醋,只尝其原味。每个人分到六只蟹,迭番煮之,使蟹的每个部位皆独具风味:膏腻堆积如玉脂珀屑,紫螯巨如拳,小脚油油且肉出。但是为了不使烹煮过度而伤了风味,所以每只蟹都是个别蒸煮,再依序分食。
张岱也盛讚雪景绝妙幻化的魅力。绍兴少雪,若逢落雪纷飞,张岱总是欣喜若狂。张岱既爱初雪中的山水,也爱观察人对初雪的反应。赏雪者有孓然一人,有群聚而观者。在他笔下,从一小撮人到孑然一人,再从孑然一人自在地处在一小撮人之中,只见他的叙述随著这视野的转变而变化,透露他自己的赏雪心境。
张岱关于雪景的纪录,最早载有日期的是在天启六年十二月。当时雪盖绍兴城,深近三尺,夜空霁霁,张岱从自家戏班裡找了五个伶人,同他一起上城隍庙山门,坐观雪景。「万山载雪,明月薄之,月不能光,雪皆呆白。坐久清冽,苍头送酒至,余勉强举大觥敌寒,酒气冉冉。积雪欱之,竟不得醉。马小卿唱曲,李岕生吹洞箫和之,声为寒威所慑,咽涩不得出。三鼓归寝。马小卿、潘小妃相抱从百步街旋滚而下,直至山趾,浴雪而立。余坐一小羊头车,拖冰凌而归。」
六年后,也是在腊月,又下了一场大雪,纷飞三日不止。这回张岱自绍兴渡河过杭州,张家和一些亲友在西湖畔都有房舍。天色渐暗,张岱著撬衣、举火炉,登小舟,要船家往湖心亭划去。此时人声鸟鸣俱绝。霜降罩湖,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应俱白,此番变貌令张岱欣喜:「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了亭上,居然已有两人铺毡而坐,奴僕正在温酒。这两人是从两百多里外的金陵而来,张岱跟他们喝了三碗酒才告辞。船家驶离湖心亭时,张岱听到他喃喃滴咕:「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出游时,主要是张岱与亲友之间在交谈,向来没有僕侍与船家开口的份。但有时虽然僕役船家在一旁张罗,并不言语,但也是此情此景所不可少的。张岱少时曾在绍兴城内庞公池附近读书,总会在池中留一小舟,兴致一来便可外出。池水入溪流,纵横交错,穿越城镇,旁有屋舍巷弄。无论月圆月缺,也不论什麽时辰,张岱总会招舟人载他盘旋水道稍游一番,舒展身心,慵懒欣赏夜色在幽冥中流逝。
有次出游,张岱是这麽写的:「山后人家,闭门高卧,不见灯火,悄悄冥冥,意颇妻恻。余设凉簟卧中看月,小傒船头唱曲,醉梦相杂,声声渐远,月亦渐淡,塔然睡去。歌终忽寤,含糊讚之,寻复鼾齁。小傒亦呵欠歪斜,互相枕藉。舟子回船到岸,篙啄丁丁,促起就寝。此时胸中浩浩落落,并无芥蒂,一枕黑甜,高春始起,不晓世间何物谓之忧愁。」(节录)
第八章 繁华靡丽皆成空
我们已无法追索,张岱是否早计画好要避开方国安与鲁王的朝廷,他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具体记述,得见他至绍兴西南百里隐居的三年,到底是何景况。此地山陵崎岖难行,多是孤村,蓊鬱山林,间或几座寺庙错落。张岱在一首诗裡提过,顺治三年,他隐居山寺几个月,仅带一子、一僕为伴,隐姓埋名,又把心力放在撰写明史上头。经过月馀,因身分曝光,被迫避他寺再度藏身,与和尚们同住了一段时间。张岱提到他飢肠辘辘,无米可炊,甚至没有柴薪举火,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中国自古以来流传忠心耿耿的隐士,宁可饿死山中,也不愿侍奉二主的故事,与事实差距甚远。张岱如今体悟到,这些品德崇隆之士,真的是活活饿死的。
张岱不愿做满人打扮,薙头蓄髮,自知模样十分吓人:「披髮入山,駴駴为野人」,张岱形容自己看起来就「如毒药猛兽」。他时常兴起自杀的想法,不过撰写明史大业未竟,又使他打消了却残生的念头。
顺治三年,年届四十九岁的张岱,颠沛流离,昔日生活的点点滴滴萦绕脑海,回忆如电袭来。张岱提到,夜气方回,鸡鸣枕上,拂晓时分,往事总入梦。值此之时,张岱告诉我们,「繁华靡丽,过眼皆空。」记下昔日回忆本是无心插柳,没想到得以为困顿生活暂时解忧:「饥饿之馀,好弄笔墨。」对张岱而言,夜间灯火星耀,琴声悠扬,腐臭难闻的牲祭,娼妓若有所思的静默,浪掷千金于古玩,母亲喃喃的祝祷,年轻伶人的粉墨登场,舟船、轿舆之旅,与知交好友的谈诗论艺,连同无数的片刻,全都值得说、值得记。
不过,张岱在《梦忆》一书的序文中强调,这些篇章不落俗套,自成一格:「不次岁月,异年谱也;不分门类,别志林也。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这年岁暮,张岱发觉他就这样写了一百二十馀篇的陈年旧事。回忆如梦片断,虽然张岱有意不写长,文章篇幅从一段至多两页不等,但编成小书也绰绰有馀了。
《梦忆》序文意象丰富,张岱一方面强调经历、感触的捕捉是随性的,但他也想使人明白,他很清楚自己追寻过去是为了什麽:「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张岱心中,这毋宁变成一道赎罪的功课,诚如他在序文所表露的:如今他所捱受的种种劫难,正是往日骄奢淫逸的报应。张岱提到自己:「以笠报颅,以蒉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苎报絺,仇轻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粻,仇甘旨也;以荐报?,以石报枕,仇温柔也;以绳报枢,以瓮报牖,仇爽垲也;以烟报目,以粪报鼻,仇香豔也;以途报足,以囊报肩,仇舆从也。种种罪案,从种种果报中见。」
不论张岱内心是否觉得,他该为昔日挥金如土的生活承受报应,他的感怀终究是超脱了时代或个人动机,不减损其感染力。某种程度上,也许张岱真是每成一段便坦白佛前,以能「一一忏悔」。然而,这些他自身与其他人生活的种种过往片刻,他又是用情至深,下笔不辍,诚如张岱在序的最后所言,「坚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
尤其在颠沛流离的头一年,张岱常以中国最受称颂的隐逸诗人陶渊明7为慰藉。早在好多年前,张岱便以陶渊明的姓取别号或书斋名,且因母亲娘家亦姓陶,让他共鸣更深。张岱想效法陶渊明并非只是毫无理由的迷恋:陶渊明的诗一千二百年来深植人心,生动传达饱学之士一心抛却壮志、功名的性情与层层肌理,或为返归故里,躬耕寸土之地,或专心为文,或如他寄情杜康,沉吟人生之梦幻无常。人皆知陶渊明好酒,为了有酒喝可以说是排除万难,有时甚至拿妻子买米的钱或不顾颜面向友人乞讨。顺治七年(一六五○年),张岱的友人陈洪绶为表彰陶渊明嗜酒如命,还从其诗中摘录饮酒轶事,绘成一系列情理兼具的画作。而不好杯中物的张岱,在顺治三年,留下与陶渊明作品唱和的诗作:包括陶渊明的〈咏贫士〉七首,关于弑主窜位的政治诗,〈自祭文〉,以及穷之有道的名诗〈有会而作〉。陶渊明于此诗中说: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飢,
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
陶渊明在诗作序文裡,对躬耕自食艰辛的梗概描述颇令人动容:「旧穀既没,新穀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裁通;旬日已来,始念飢乏。岁云夕矣,慨然咏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
陶渊明〈咏贫士〉七首的开篇之作最为脍炙人口。该诗旨在传达回归田园生活的寂聊,以及陶渊明本人的榜徨无依,「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两句尤其佳。历代文人雅士的品评,无不认为陶渊明这首诗不仅喻指自己,也暗喻所处朝代的崩溃。张岱亦以组诗七首唱和陶渊明,顺治三年秋天,他在风雨凄然之时提笔,特别提及要跟「诸弟子」分享,张岱当时基于安全理由将之送往城东山中。
陶渊明〈咏贫士〉第一首如下:
万族各有託,孤云独无依;
暧暧空中灭,何时见馀晖。
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
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
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飢?
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张岱的唱和虽仿效陶渊明,不过换了一个重要隐喻:陶渊明的不祥之云成了萤火虫,在霏霏淫雨中光芒终于熄灭。张岱写道:
秋成皆有众,秋萤独无依。
空中自明灭,草际留微晖。
霏霏山雨湿,翼垂不能飞。
山隈故盘礡,倚徒复何归。
清当晚至,岂不寒与飢?
悄然思故苑,禾黍忽生悲。
无论张岱是否夸大境况的凄凉─逃离绍兴后,他说,所有家当仅存「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 ─他始终感受到昔日世界的牵繫。张岱并未吐露一六四○年代后期的生活细节,不过到了顺治六年(一六四九年),他已决心重返绍兴。
此番还乡,人事全非。是因方国安的手下也好,遭当地强梁打劫也罢,或新朝满清官员要他为两度支持鲁王付出代价,总之张岱已是无家可归。顺治六年十月,张岱在绍兴龙山后麓赁租一块地,这裡曾是他卜居、读书、赏灯、观雪的地方,他常与祖父张汝霖偕游的「快园」同样在此。儿少时代的快园宛如人间天堂,其名取自在此读书为一大快事:其间果树茂密,池塘广阔,花木扶疏、围牆拱立,景致之开展,彷彿人信步在卷轴上。在明朝灭亡前的繁盛年代,拥有一座园子还能取得丰厚的投资报酬。张岱写道,快园裡池广十亩,养鱼鱼肥,鲜橘可易丝绸,甘蓝、甜瓜、桃、李一天可卖一百五十钱─真可谓「闭门成市」。
不过,等张岱赁居于此,快园早已一片荒芜。当年快意的读书人杳然不复见,家族四散飘零。张岱说他得亲自修葺这败屋残垣,然而造景的木石格局有何深意就无法索骥了。张岱以戏谑之说告诉老友,快园之名,证实了中国人「名不副实」的成语。这就好比「孔子何阙,乃居阙里;兄极臭,而住香桥;弟极苦,而住快园。」
编辑:陈佳
关键词:史景迁 人生之乐乐无穷 繁华靡丽皆成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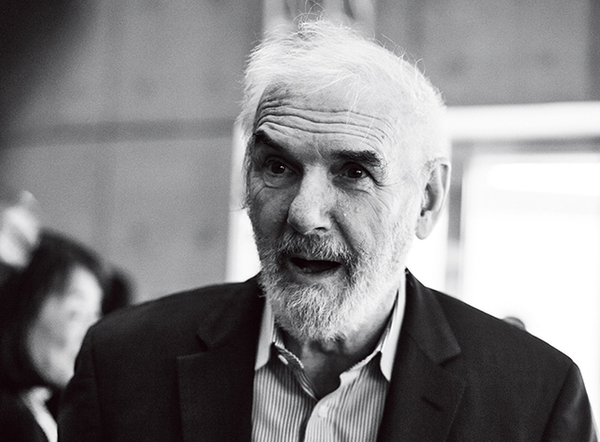


 贵阳机场冬日为客机除冰 保证飞行安全
贵阳机场冬日为客机除冰 保证飞行安全 保加利亚古城欢庆“中国年”
保加利亚古城欢庆“中国年” 河北塞罕坝出现日晕景观
河北塞罕坝出现日晕景观 尼尼斯托高票连任芬兰总统
尼尼斯托高票连任芬兰总统 第30届非盟首脑会议在埃塞俄比亚开幕
第30届非盟首脑会议在埃塞俄比亚开幕 保加利亚举办国际面具节
保加利亚举办国际面具节 叙政府代表表示反对由美国等五国提出的和解方案
叙政府代表表示反对由美国等五国提出的和解方案 洪都拉斯首位连任总统宣誓就职
洪都拉斯首位连任总统宣誓就职
 法蒂玛·马合木提
法蒂玛·马合木提 王召明
王召明 王霞
王霞 辜胜阻
辜胜阻 聂震宁
聂震宁 钱学明
钱学明 孟青录
孟青录 郭晋云
郭晋云 许进
许进 李健
李健 覺醒法師
覺醒法師 吕凤鼎
吕凤鼎 贺铿
贺铿 金曼
金曼 黄维义
黄维义 关牧村
关牧村 陈华
陈华 陈景秋
陈景秋 秦百兰
秦百兰 张自立
张自立 郭松海
郭松海 李兰
李兰 房兴耀
房兴耀 池慧
池慧 柳斌杰
柳斌杰 曹义孙
曹义孙 毛新宇
毛新宇 詹国枢
詹国枢 朱永新
朱永新 张晓梅
张晓梅 焦加良
焦加良 张连起
张连起 龙墨
龙墨 王名
王名 何水法
何水法 李延生
李延生 巩汉林
巩汉林 李胜素
李胜素 施杰
施杰 王亚非
王亚非 艾克拜尔·米吉提
艾克拜尔·米吉提 姚爱兴
姚爱兴 贾宝兰
贾宝兰 谢卫
谢卫 汤素兰
汤素兰 黄信阳
黄信阳 张其成
张其成 潘鲁生
潘鲁生 冯丹藜
冯丹藜 艾克拜尔·米吉提
艾克拜尔·米吉提 袁熙坤
袁熙坤 毛新宇
毛新宇 学诚法师
学诚法师 宗立成
宗立成 梁凤仪
梁凤仪 施 杰
施 杰 张晓梅
张晓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