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书画·现场>讯息讯息
重寻现代美术史的“药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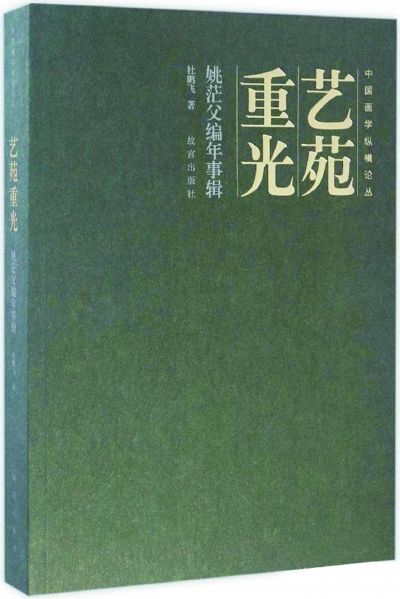
《艺苑重光:姚茫父编年事辑》
杜鹏飞 著
故宫出版社
2016年9月版
民国初年特别是北京政府时期(1912—1928)的北京艺坛,夹在“旧”与“新”之间,面貌值得仔细“打量”,而其入眼处,正是所谓“京派”画家,其中又以陈师曾、姚茫父等为冠。神器更易,时势变换,文化观念和审美风尚层面也产生种种冲突,“京派”不唯力图反思“传统”、开创“现代”,亦且一向被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反向力”,对这些艺文巨子的生平、思想、交游、立场详加考究,当于了解彼时文化生态与格局不无裨益。
晚近以来的艺术,几乎已在相当程度上被意识形态化,有关20世纪初的美术史,我们最为耳熟能详的命题可能就是“美术革命”。叙述者让我们感觉到,画坛已是一个战场,充满着你死我活的剧烈争斗,声势浩大、顺势而赢的,当然就是素承天祚的“写实主义”,其天然具备的人民性和革命性,是中国画跳脱出重重困障走向“现代”、拥抱世界的保证。
然而真正的历史可能是,“美术革命”在当时并没有立刻形成实际的力量,响应者寥寥,即使我们去考量这个话题最早产生的境况,也存在着答非所问、“鸡同鸭讲”的尴尬:1918年底到1919年初,吕澂和陈独秀就“美术革命”的通信,一个是对因西画引入产生的混乱局面感到焦虑,希望艺术界在学理上重新澄清什么才是社会所需的艺术,另一个则直接表示要清扫“四王”及其影响,并主张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自救”。有意思的是,晚清民初“四王”(尤其是王石谷)最忠实的拥趸,同时也是当时北京画界最具影响力的画家之一陈昔凡,正是“四王”最有力的反对者陈独秀的嗣父。
虽然有关“美术革命”的讨论没有再继续进行下去,却在后来被视为近现代美术发展一个重要脉络的源头,“新”派和“旧”派如此泾渭分明、剑拔弩张地“共生”着,尤其是在共和国建政之后,反过头来回顾“庶民的胜利”之路,更觉“美术革命”是一股洪流,作为承载“封建专制制度”的艺术趣味,旧的美术必须接受“写实主义”以革其命,“写实主义”或“写实精神”成为大破“旧牢笼”的利斧,它既是称手的工具,又是“政治正确”的文化资源。
在这种“主流”艺术史的观照之下,民初北京画家和晚清“四王”余绪一道,被毫不犹豫地打包起来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是被革命的对象和历史的“杂音”,即使他们在当时“尚未足以自立”的徐悲鸿眼中是一群“已为北京之选”的人物,但似乎依然逃不过被斥为“最封建”“最顽固”之“堡垒”中人的命运。
《艺苑重光:姚茫父编年事辑》就是一本有关“革命对象”的“杂音集”,它是作者杜鹏飞积十余年心力著成的一部有关姚茫父的“年谱详编”,实际对谱主的朋友圈也多有涉及,由此再现出民国初年北京画坛文人交游的丰富多彩,重申了民初十余年间北京画坛景象实与晚清时期迥异的观点。令人没想到的是,这“杂音”竟能够如此纷繁而悦耳,甚至可以作为重新形塑现代美术史的一副“药引”。杜先生本职是环境工程专业教授,科研之余,对书法和艺术史最为留心用力,2014年清华大学成立艺术博物馆,杜先生即受命主持该馆日常事务。我记得以前曾听他谈及艺博馆的发展方向和策略,是要“立足经典收藏”和“面向未来收藏”,在选择艺术家作品的时候,特别注意要超脱于市场,甚至自觉与市场保持一定的距离。读到这本《事辑》,回过头想想杜先生的话,发觉他对“超脱于市场”或曰被市场严重忽视的重要艺术家,实在是抱有一贯的敏感和倾心。
作为彼时北京艺林并称的领袖人物,姚茫父和陈师曾有许多相似之处,徐悲鸿在《四十年来北京绘画略述》中称姚“样样都来,但未必工”,谓陈“画与书略有才气,诗乃世家,以能集诸艺于一身,故为时所重”,大抵指责二人博而不精。不过,这“博而不精”几字太容易成为贬斥他人的一句套语,其实在美术界,即使是学术文艺特为昌隆的民国时代,真正才备多能之人,为数仍少,姚茫父和陈师曾则是确确实实的通才,无论在小学、诗文、书画、金石等方面,都卓有造诣,且能承古开新,气象不局。可惜的是,二人皆未享高寿,因此在很多领域的影响力实不如那些长年深耕一艺的专门家,声名因此不彰,更非后世的“市场宠儿”;但也正由于他们涉猎广博,留下纷杂多样的各式作品和史料,静俟有心的后来者搜隐抉微,重现其艺术生命和特殊影响。
此书之名大概正有这样的意思。作者搜聚使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以事系年,客观而详尽地展现姚茫父五十五岁的人生旅迹和学艺生涯,同时也客观重现了民初北京艺坛的兴盛光景,大体论之,《事辑》之特点有三:
第一,“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姚茫父虽年未及耳顺即以病谢世,但因创作精力旺盛,又与政、商、学、艺、文教各界人物交往广泛而密切,故而可录写之手迹与事迹甚多,《事辑》所述所考,做到了详略得当,将不少他处已见的文献和不甚重要的日常书札、应酬文字等略提其要,至于较为稀见的文字,则在说明基本事实的同时酌情引录。如提及民国十四年腊月寿苏雅集,姚茫父与同社友人为谭篆青各作《聊园填词不达意图》裱为长卷事,《事辑》细致迻录卷尾诸家题跋,因知“三十年来故都有社事之变迁”。
第二,史料丰赡,“物”“事”互证。姚茫父博通诸艺、桃李满京,留下数量可观的诗稿、文章、著作、书画、题跋、拓本、刻铜器物以及从政从教时期的文件资料等,作者时时留心,从公私藏品及历年拍卖会、展览会所见大量姚氏作品之中,挑选出绝少争议者,系于行年事迹之下,或以有纪年的姚氏作品与其自记诸事比对,力求丰富完善。
第三,留心谱主思想,绝非记流水账。年谱的撰写有不同的形式,“年谱长编”近似一种材料汇集,虽极详实,但仍如散沙,尚要留待异日加以淬炼成章,《事辑》则自有取舍裁断,尤其对于体现姚茫父教育思想、艺术主张的材料,不肯轻易放过。如姚氏1916年致信蹇季常批评教育界主管、1927年与邓和甫通信讨论绘画时反对将画视为“美术”,如简单视之为了解姚茫父与友人一般交往的资料,则不免对它们有所亏待。
值得一提的是,书前所缀谈晟广先生长文《开创“现代”的“传统”——读〈艺苑重光:姚茫父编年事辑〉再认识民国初年艺术史》,涉及民国初年艺术史的建构、日本对于“现代中国”发现自身“传统”价值的推动、姚陈二人辉映下的北京画坛等话题,可谓一种“背景介绍”,不妨视为《事辑》的“导读”。民初“京派”画家之间的互动,以及他们与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的交往,十分频繁和深入,画家们不仅利用组织画会、办设展览来集中公私所藏资源以研究传统,同时还积极与日本开展艺术交流,如持续举行中日绘画联展、讨论并出版美术研究论著等,不论是姚茫父,还是陈师曾和金城,都是其中特为活跃且极具影响力的中坚。在进入姚茫父的艺术世界以前,阅读谈先生所撰长文,能够先行大致了解姚氏所处的现实世界,这或许也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
编辑:杨岚
关键词:重寻现代美术史的“药引” 现代美术史



 中国制造助力孟加拉国首条河底隧道项目
中国制造助力孟加拉国首条河底隧道项目 澳大利亚猪肉产业协会官员看好进博会机遇
澳大利亚猪肉产业协会官员看好进博会机遇 联合国官员说叙利亚约117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联合国官员说叙利亚约117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伊朗外长扎里夫宣布辞职
伊朗外长扎里夫宣布辞职 中国南极中山站迎来建站30周年
中国南极中山站迎来建站30周年 联合国特使赴也门斡旋荷台达撤军事宜
联合国特使赴也门斡旋荷台达撤军事宜 以色列前能源部长因从事间谍活动被判11年监禁
以色列前能源部长因从事间谍活动被判11年监禁 故宫博物院建院94年来首开夜场举办“灯会”
故宫博物院建院94年来首开夜场举办“灯会”
 法蒂玛·马合木提
法蒂玛·马合木提 王召明
王召明 王霞
王霞 辜胜阻
辜胜阻 聂震宁
聂震宁 钱学明
钱学明 孟青录
孟青录 郭晋云
郭晋云 许进
许进 李健
李健 覺醒法師
覺醒法師 吕凤鼎
吕凤鼎 贺铿
贺铿 金曼
金曼 黄维义
黄维义 关牧村
关牧村 陈华
陈华 陈景秋
陈景秋 秦百兰
秦百兰 张自立
张自立 郭松海
郭松海 李兰
李兰 房兴耀
房兴耀 池慧
池慧 柳斌杰
柳斌杰 曹义孙
曹义孙 毛新宇
毛新宇 詹国枢
詹国枢 朱永新
朱永新 张晓梅
张晓梅 焦加良
焦加良 张连起
张连起 龙墨
龙墨 王名
王名 何水法
何水法 李延生
李延生 巩汉林
巩汉林 李胜素
李胜素 施杰
施杰 王亚非
王亚非 艾克拜尔·米吉提
艾克拜尔·米吉提 姚爱兴
姚爱兴 贾宝兰
贾宝兰 谢卫
谢卫 汤素兰
汤素兰 黄信阳
黄信阳 张其成
张其成 潘鲁生
潘鲁生 冯丹藜
冯丹藜 艾克拜尔·米吉提
艾克拜尔·米吉提 袁熙坤
袁熙坤 毛新宇
毛新宇 学诚法师
学诚法师 宗立成
宗立成 梁凤仪
梁凤仪 施 杰
施 杰 张晓梅
张晓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