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人物·生活>悦·生活悦·生活
汪晖:回忆唐弢先生
一
1988年和1989年,我两次陪老师唐弢先生住在宾馆,写《鲁迅传》。如果记得不错的话,一次是1988年秋天,一次是1989年春天。第一次在北京十三陵旁边的明苑宾馆,第二次在城里的国谊宾馆,我们住在一个房间里,谈很多事。每天我自己读书,他写作,写完一节,就给我看,我们两个人讨论。他希望我提意见,让他来改。有时他说需要什么书,我就回城里借。
1988年秋汪晖(左)与唐弢在一起
那时我刚刚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毕业留所工作。毕业前有师生长幼这层关系,毕业后还是师生,但又有点像师友。他一再对我说,学生毕业了就是朋友,是同事。
住在一起,又没有别人,话就多了。唐先生比较有意识地跟我谈话,原因大约有两个:一个是跟我谈鲁迅,一个也是他老了,需要一个年轻的、信得过的、了解他的思想和经历的人。
每天晚上他都跟我说话。老人睡觉打呼噜,很响。因此他跟我说着说着,直到我累得不行,睡着了,他自己再躺下。到第二天早晨,他很早就醒,怕吵醒我,就半靠在床上不起来,等我醒来。每天都是这样。我醒来就见他在对面床上穿着睡衣睁着眼睛看着我,说,哦,醒了。
有一天晚上我们俩聊天,聊到个人生活,就讲起小说,讲人生经历、信仰、爱情故事,讲到了托尔斯泰、马尔克斯。第二天早晨,唐先生看着我醒来,就那样看着我说:“我在想托尔斯泰出走的问题。年轻时无论如何不懂,为什么托尔斯泰要出走。现在到了这个年纪,开始有点明白了。”
我很惊讶。或许头一天晚上谈及文学与爱情,我的第一反应集中于这方面。师母对唐先生非常好。而且唐先生曾经跟我说过,他对师母很歉疚。唐先生曾对我发过一次火,是我们1985年一起去杭州开会。那次他下轿车时碰伤了手,会议方安排我跟他一起住,方便照顾他,就住现在的标准间,两张床。他就跟我发火,说,来之前你不告诉我,这个地方是可以住两个人的。
我说我好像跟您说过。研究生院组织会议时我就跟您说过,您是单独一间,我们学生是两人一间。
他很生气地说,你肯定没有跟我讲,如果你说了,我一定会记住的。
过了一天,他大概觉得自己的发火有点让我为难,就给我讲了缘由。唐先生有过两次婚姻。他的亡妻,是抗战时“孤岛”时期在上海贫病交加中死去的。那时唐先生本来在邮局工作,为了不跟日本人合作,就辞掉了邮局的工作,辞职就没有收入了。这一年当中,母亲、妻子、两个孩子,一家四个亲人体弱病死。
所以“孤岛”时期,他写了《落帆集》,左翼友人曾批评其风格太悲观。可是,因为拒绝在日本占领时期继续在邮局工作,他一年当中家里死掉四个人。你可见,像他这样的人,对于战时与日本人合作的事情,在态度上肯定是决绝的。所以1988年前后,关于周作人附逆问题,有许多讨论,一些论者从不同方面为周作人辩护。唐先生与周作人有交往,他年轻时,周氏兄弟对他都有影响,但在政治上、在感情上,他都不会赞同为附逆翻案。
唐先生是农民的孩子,在邮局从工人做起,到“孤岛”时期,已经做到二等邮务佐,当时算比较好的工作。后来邮局被日本人占领,再工作就等于为日本人工作,他就拒绝继续在这里工作。不工作,家里没有了收入,就出了这样的事。那时候他非常悲观,文章也低沉。到后来外人才知道他家一年中死了这么多人。
在“孤岛”时期的上海,他和柯灵等人继续从事抗日文艺运动,合作编辑《周报》等。妻子过世后,他一个人鳏居7年,带一个孩子。7年后有了第二次婚姻,就是我的师母沈絜云老师,沈老师的父亲是国民党邮政总局次长。
这是唐先生的第二次婚姻。杭州开会时,他为什么跟我发火呢?沈老师当年是大学生,毕业以后由父亲安排来邮局工作,认识了唐先生,两个人是自由恋爱。当时唐先生在上海已经颇有文名。沈老师家里知道以后,阻止他们俩结婚,原因一方面唐先生是左派文人,另一方面在家庭背景上,唐先生家里比较穷,又结过婚,二人年纪相差七八岁。
父母不同意,把沈老师关在家里,不让她出去,又把她带去南京,过段时间,又要给她介绍男朋友。沈老师就急了,捎信给唐先生说,“你若是不想办法,这就没有办法了。”唐先生就从上海偷偷跑到南京来,两人见面当天就坐了火车一同回上海,到上海第二天就找沈钧儒证婚。这是预备打官司的,因为沈老师家地位高,所以要找位有名的大律师来证婚,登报。也是怕沈老师家里势力范围大,登报的同时,他们就去了杭州,等于躲一下。两人蜜月是在杭州过的。从此之后,二人再没有一起来过杭州。
所以唐先生说,倘若知道旅馆可以两个人住,他必定会带沈老师来。
几年后,在国谊宾馆,那个早晨,他75岁,跟我说他理解了托尔斯泰。意思说,他也想出走。他说,人的思想和感情生活这个东西很复杂。托尔斯泰晚年的出走,解说的人多半集中于他与夫人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他的出走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史事件。他与宗教的关系,他对前半生生活的内疚,他名声显赫而为出于不同目的的人包围,甚至在出走途中,在那个终结其生命的小站,他也没有摆脱“崇拜者”的包围与隔离。
不过,唐先生的人生经历、性格、思想和情感世界,都不好拿来与托尔斯泰比附,只是托尔斯泰的出走触动了他的某种思绪。
二
写《鲁迅传》是唐先生的长久心愿。很早,或许是上世纪50年代,他就曾经写过一个简略的传记。《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鲁迅部分是他亲自执笔写的,水平很高。他出版了那么多关于鲁迅的研究和考证文章,对鲁迅生平可算烂熟于心,最终却没有完成他的鲁迅传。原因是什么?除了时间不断被人占去———索序的、索文的,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研究工作———之外,评价鲁迅实际上要讲的是现代史。
唐先生手稿一开头就讲绍兴,由此勾连起一系列事件,从禹陵、鉴湖、徐文长的故事,到太平天国运动,还有义和团运动,复仇雪耻的传统,以及刀笔吏绍兴师爷的故事等,这是鲁迅生活的氛围,这些也正是历史观变迁的基本路径,该怎么看这些?
唐先生要重新诠释鲁迅,即便聚焦于个人的生平和思想,也必须从对太平天国、义和团的再认识开始。这是很严峻的问题,我觉得唐先生没真正解决那些矛盾,或者说他用他的方法解决了那些问题,但这些问题今天依然是问题。他对旧中国是有判断的,对帝国主义是有基本论述的———对于近代中国的基本处境,他怎么可能没有最基本的态度?他毕竟还是过来人。但是,要解释这些历史现象仅仅有这样的范畴显然不够。他常常提及《左传》、《史记》的传统,尤其赞赏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但即便如此,历史叙述背后离不开史识和史观。
新的时代使重新理解鲁迅、重新评价“五四”变成一个问题。因为鲁迅是和现代史联系在一起的,除审美、个人史外,对他的任何判断都牵涉到其他历史判断。所以这成为一个问题,一个难处。即便写个人史、生平也关乎历史事件的重新解释。
唐先生希望把这些说得更加周全、平衡一些。《鲁迅传》就写得困难。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唐先生就协助许广平编《鲁迅全集》了。他计划写《鲁迅传》应该很早,可能“文革”以前就有计划。这本书酝酿已久,他自己需要写出来,同时这也是很多人的期待。我多多少少地觉得,大家对他的期望造成了负担,他的自我期待也造成了某种重负。相比于他的其他一些文章,比如《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关于周作人》、《关于林语堂》、《关于新诗》的漂亮、松弛,如同行云流水,将艺术洞见与时代氛围和盘托出的方式,他关于鲁迅的写作似乎要重很多。他为《反抗绝望》所写的序言,也比他同时期写其他题材的文章显得更重一些。在这篇序言中,他侧重谈及了尼采等,这个要素是他在生活最幽暗的早年时期就谈及的,现在又在他的晚年写作中出现了。
为什么一写鲁迅,就重得不行?首先他把这事看得很重。他写《鲁迅传》,是一再拖延,到最后才动笔,我觉得他那时找到感觉了。多年的心愿到晚年找到了一些新感觉。即便如此,他一定让我住在宾馆陪他写,说明他还是有一些不确定的东西。除了前面提及的历史问题,如何解释鲁迅,也还有许多需要考虑的地方。他说得很清楚,就是希望能讨论一下,每写一章、每写一小节,几千字,都要求我看一看,讨论过后他再继续。
他曾经回顾说,他最初考虑的标题叫《鲁迅:一个天才的颂歌》,大概是上世纪50年代就形成了,到上世纪80年代初刚动笔时也还是如此。那时他怎么考虑,我没参与;我跟他念书时,他已经将标题改成了《鲁迅:一个悲剧的灵魂》。两个意思不同,或者更准确地说,调子不同。为什么这样改?我说不清,我不能代他解释。我感觉到晚年,他思想处在某种变动当中。根本的东西没有变,什么变了呢?我说不好。
唐先生成为鲁迅专家不是因为和鲁迅个人关系深。虽然认识鲁迅,但在鲁迅周围那一圈青年中,唐先生是“外围”吧,他那时还很年轻。唐先生出身农民,贫苦社会里出来的。要知道他不是左翼进步学生,他是工人运动里头的,在邮局当分信工,很重的劳动。一个农民的孩子来到上海,所谓寄人篱下,初中二年级就失学,当邮政工人,从学徒做起,年轻,没有别的背景,就是写文章。那时的唐先生对鲁迅就是学生样子,完全是仰望。他个人特别崇敬鲁迅,这是年轻时候奠定的,鲁迅对于下层的描述和最深的同情首先触动了他。渐渐地,他变成了鲁迅专家,鲁迅思想的阐释者。
唐先生出生于1913年,1992年去世,去世时79岁。
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上,在鲁迅研究的历史上,唐弢先生是位重要人物,是学科奠基者之一,也是我的老师。
唐先生是个典型的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待人接物有传统文人的风格,不仅是温和,而且有一些内部的狂狷。
唐先生是个正直的人。他文字上的严谨也是很清楚的,他品评人物,表现在笔底春秋上,调子是严正的。这个分寸其实很不容易。
对知识分子来说,慎思明辨、把握问题的能力是关键的。若没有这个能力、洞见,做个普通人可以;若不在浪潮当中,也可以。若在浪潮中,躲也躲不了。知识分子与时代相呼应,需要胆识也需要洞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自知之明,不能过于自恋。即便自己并非为名或利,如果缺少真正的历史洞察力和时代判断力,最终只能误人误己。其实有时也误不了谁,或就只是一个笑话。那些不是把时代的课题当成自己的课题,而是将自己的意念当成时代的课题的人,不免如此的。
或许有鉴于此,唐先生才反复说要爱惜羽毛和有所不为吧。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本文发表时有删节,全文将在《文史资料选辑》刊发。)
编辑:邢贺扬
关键词:唐弢 汪晖 回忆 《鲁迅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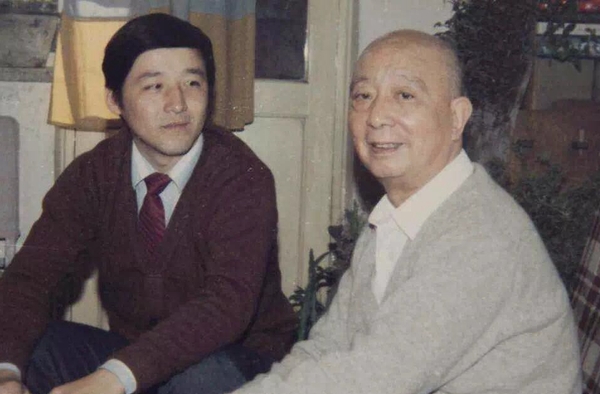


 贵阳机场冬日为客机除冰 保证飞行安全
贵阳机场冬日为客机除冰 保证飞行安全 保加利亚古城欢庆“中国年”
保加利亚古城欢庆“中国年” 河北塞罕坝出现日晕景观
河北塞罕坝出现日晕景观 尼尼斯托高票连任芬兰总统
尼尼斯托高票连任芬兰总统 第30届非盟首脑会议在埃塞俄比亚开幕
第30届非盟首脑会议在埃塞俄比亚开幕 保加利亚举办国际面具节
保加利亚举办国际面具节 叙政府代表表示反对由美国等五国提出的和解方案
叙政府代表表示反对由美国等五国提出的和解方案 洪都拉斯首位连任总统宣誓就职
洪都拉斯首位连任总统宣誓就职
 法蒂玛·马合木提
法蒂玛·马合木提 王召明
王召明 王霞
王霞 辜胜阻
辜胜阻 聂震宁
聂震宁 钱学明
钱学明 孟青录
孟青录 郭晋云
郭晋云 许进
许进 李健
李健 覺醒法師
覺醒法師 吕凤鼎
吕凤鼎 贺铿
贺铿 金曼
金曼 黄维义
黄维义 关牧村
关牧村 陈华
陈华 陈景秋
陈景秋 秦百兰
秦百兰 张自立
张自立 郭松海
郭松海 李兰
李兰 房兴耀
房兴耀 池慧
池慧 柳斌杰
柳斌杰 曹义孙
曹义孙 毛新宇
毛新宇 詹国枢
詹国枢 朱永新
朱永新 张晓梅
张晓梅 焦加良
焦加良 张连起
张连起 龙墨
龙墨 王名
王名 何水法
何水法 李延生
李延生 巩汉林
巩汉林 李胜素
李胜素 施杰
施杰 王亚非
王亚非 艾克拜尔·米吉提
艾克拜尔·米吉提 姚爱兴
姚爱兴 贾宝兰
贾宝兰 谢卫
谢卫 汤素兰
汤素兰 黄信阳
黄信阳 张其成
张其成 潘鲁生
潘鲁生 冯丹藜
冯丹藜 艾克拜尔·米吉提
艾克拜尔·米吉提 袁熙坤
袁熙坤 毛新宇
毛新宇 学诚法师
学诚法师 宗立成
宗立成 梁凤仪
梁凤仪 施 杰
施 杰 张晓梅
张晓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