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人物·生活>悦·生活悦·生活
韩书力:吴作人先生的西藏情结
美协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前一段吴先生洗澡不慎摔伤了腿,本来医嘱是决不可出门的,只见吴先生笑微微地说:“这个展览是青藏高原的联展,有十几个民族画家的作品,意义不一般哪。再说,我早答应过人家要来的呀。”那位女弟子又是一句京白:“你也不看看自己的情况!”吴先生品了一口茶,仍是那般平静地自语道:“做人做事要忠厚老实啊。”
吴作人
吴作人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自1998年以来,作为晚辈后生,笔者每年赴京公干期间,总要捧上一束百合与玫瑰组合的鲜花到西郊花园村吴府去看望萧淑芳先生和挂在客厅正壁上吴先生的肖像,借以表达景仰之情。有一年两会期间,当我再次手捧鲜花赶到花园村吴府,迎接我的已是吴、萧二位先生的女儿萧慧大姐了,而不是坐在轮椅上微笑着的萧先生了,因为萧先生已于前一年冬至时节赶到另一个世界去与吴先生团聚了。此时此境,萧先生也以肖像的形式与吴先生并肩,在素洁的墙壁上向我,向所有的来拜望他们的学生与友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吴先生享年89岁,萧先生享年94岁,作为画家他们早已功成名就,各领风骚;作为教授,他们早已是桃李满天下,艺坛杏坛硕果累累。所以,从终极意义上讲,他们的微笑是自然的、幸福的和永恒的。吴作人先生上世纪40年代初曾数次到青海、甘肃、四川深入藏区生活旅行写生,从而逐渐创造出独属于他,也独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系列撼人心魄的艺术形象——雪野上的奔牦、大漠中的骆驼、展翅重霄的雄鹰等。
由于种种原因,吴先生竟始终没能踏上真正意义上的西藏地区,没能畅游于圣山神湖之间,这无论对于他本人还是对于西藏来讲,都不能不说是一种深深的遗憾。吴先生有一方闲章印文是“曾客通天河上”,更令我辈一次又一次品读出他老人家对地老天荒的青藏高原那种萦绕始终的情结。
作为晚辈,我无缘在正常的求学时期得到吴先生的耳提面命,只能通过印刷品和展览会上有限的作品,来学习体悟吴先生那平和隽永的书境,并进而推衍与想象从作品里流露出的吴先生的风采与精神。1975年夏,我在拉萨斗胆向吴作人先生万里投书讨教画技与画理,很快便收到了由李化吉老师转寄来的有吴先生亲笔签名的数幅中国画印刷品和其当年在康青藏区画的人物肖像速写石印件,令我激动不已。
1977年夏,我出差到北京,为了感谢吴作人先生远天远地的关切之情,我特意在八廓街选购了一把小藏刀作为见面的小礼品,同时还不知深浅地带上了自己刚刚完成的一套反映藏民生活题材的连环画《会说话的琴轴》,想借机一并得到指教。记得那是个难得凉爽又难得清静的夜晚,吴先生在画室的台灯下,仔仔细细地一张一张地审视着画稿,还不时地抽出若干幅给予点评,反倒让我十分不安,很后悔自己的轻率。吴先生一再说他喜欢这套连环画,因为有较强的生活气息与地域特点,还说要推荐给外文出版社的编辑们看看。
1979年秋,北京人民大会堂西藏厅委托我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完成一幅丈二山水画《喜马拉雅晨曦》,我从未画过山水,唯一能做的努力就是挤出时间沿雅鲁藏布江逆行几百公里,感受两岸的民情风光,画画速写,然后回拉萨闭门创作。画如期完成,西藏自治区领导审查通过,但要求保留藏文题款(为罗伦张先生题写)而挖掉汉文题款到北京请名人重题后交大会堂。我赶到北京,把这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向何溶老师诉说后,他很痛快地答应帮忙与吴作人先生联系,第三天就得到吴先生同意题字的回音,并嘱我尽快将画送到他家。那天吴先生有事外出,萧淑芳先生在家等我们。她说吴先生让我们写清楚题字是左行还是右行,因为不懂藏文,怕藏汉文相左。
一周后,我在招待所接到吴作人先生的亲笔信,命前去取画。我兴奋地赶到吴府,当我见到已题好“喜马拉雅晨曦”六个遒劲苍莽“吴篆”的画幅张挂在客厅西墙的那一刻,真是感动与愧然之情油然并生。吴先生特别说道:画上的小款“书力画作人书”似有不妥,因为藏文是别人题的,应写“作人题篆,才是,但图章已盖好,不便更改了,你回西藏向有关人士说明致意吧。这件小事过去已整整27个春秋了,但它对我和西藏美术工作者的教益却是弥久与深刻的.
我们从各种媒介上得知,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吴作人先生艺术生命最健旺的时期,正所谓人书俱老,也是吴先生艺术活动(包括社会活动)最忙碌的时期,正所谓实至名归。那段时日,我抱着不打扰就是尊敬与爱戴的信条,决定不在吴府车水马龙的当口再凑热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他的生命历程与艺术活力毕竟是有限的,因而他理应有更多的属于自己的时间与空间。
于私不打扰不难做到,而于公则是不得已,有录可查的便有198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廿周年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西藏民间雕刻艺术展”和1988年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西藏青海当代美术作品联展。这两件展事,在北京可能算不得什么,而在西藏、青海这样的边远省区则是要使出吃奶之力才能办成的。其难度有经济上的捉襟见肘,地理上的水远山遥及其他方面,不一而足。然而吴作人先生和十世班禅大师均拨冗为上述两画展开幕共同剪彩祝贺并给予实事求是的鼓励与指教。事后有人戏称当代中国佛艺界两位大师都关照,青藏美术定是前途无量。记得1988年8月上旬,我与时任青海美协主席左良登门请吴作人先生指导支持两省区联展时,吴先生平静地说,现在的画展太多,来请的也太多,看了张三的不看李四的就会造成不平衡,故而近来是一概回绝。不过青藏高原的画家们来北京办展,又是个多民族的大型画展,不容易,到时我们一定去。
8月5日联展开幕式结束之后,我们陪吴先生、萧先生回到美术馆一楼休息厅休息,这时他们的许多老朋友、老同学纷纷前来寒暄问候。我与左良兄伺茶在侧,恭听他们那忽而巴黎,忽而新中国成立前,忽而“文革”的饶有兴味的岁月切片晤对。这时有一位60上下的吴先生的女弟子走进来,还没坐定就冲着吴先生喊起来:“你不要命了,伤还没好怎么又出来了!”(美协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前一段吴先生洗澡不慎摔伤了腿,本来医嘱是决不可出门的)只见吴先生笑微微地说:“这个展览是青藏高原的联展,有十几个民族画家的作品,意义不一般哪。再说,我早答应过人家要来的呀。”那位女弟子又是一句京白:“你也不看看自己的情况!”吴先生品了一口茶,仍是那般平静地自语道:“做人做事要忠厚老实啊。”这句言者无意或有意的话,我相信,至少是我们当时在场的青藏各族画家的心中将会铭记此生。
1991年,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西藏美协编《西藏当代美术》画集,当我们赴京取吴作人先生的题签时,吴先生留我们在客厅里谈了很久。他问到拉萨的近况,我们据实回答。他还以其渊博的历史知识给我们讲了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大义。夜幕渐渐垂下,他坚持要送我们到大门口,在华侨公寓花木扶疏的小道上,我们伴随他的左右,慢慢挪着步子。吴先生边走边感慨道:“上世纪40年代初,几次努力进西藏均未果,如今方便得有飞机往来,可身体又不允许了,现在见到西藏来的同志也就如同到了西藏吧。”微风送来阵阵金银花与晚香玉的清香,吴先生目送我们登上了26路公共汽车。至今,他的身影与花香仍时时交织着出现于我们的心际眼帘。以后,来藏采风的美院老师们说,吴先生患脑血栓连续住院好几次,又说,如今吴府门前的车马倒是较往常稀疏了,不过这对一位沉疴在身的老人,倒是一件好事。
1992年春,我拟赴巴黎办第三次个展,到北京领签证和机票,很想趁机去看望调养中的吴先生,又因此时已没有了打扰与沾光之嫌,所以在招待所很坦然地拨通了吴府的电话,萧先生接听后,热情邀我前去。我进门后萧先生高兴地告诉我,吴先生听说我要来看他,中午只躺了一个小时就起床了。我跟随萧先生缓缓步入卧室,只见吴先生端坐在沙发椅上,没有戴那副很为之增加学者风采的眼镜,脸庞明显瘦了一圈。我先向吴先生行双手合十大礼,再向他老人家献上从大昭寺请来的包含着人间美好情感与祝福的阿细哈达,然后呈上我编的《西藏艺术》(雕刻卷)画集,吴先生略显激动。萧先生和我把画集捧到他的右眼一侧,吴先生用其尚存的一线狭窄的目光艰难地扫视着这本7年前他亲临剪过彩的展览作品集。接着我向他转达了西藏美协同事们对他的问候与祝福,并扼要汇报了曾到过吴府聆听过吴、萧两位前辈谆谆教诲的几位藏族年轻画家的进步,他边听边欣慰地点着已不太灵便的头,萧先生还热情地帮我们拍了合影。
当我起身告辞时,吴先生又让萧先生送我一本刚出版的《吴作人传》,我请吴先生签个大名,他迟疑了一下便握住萧先生递过去的签字笔,颤抖着签上了作人两个大字。谁知这两个字竟然写了两分钟之久……我捧着笔迹未干的厚厚的《吴作人传》不禁鼻子一酸,昔日他那驱动仙花妙笔,在布上纸上挥洒幻化出无数奇伟与美好景象的大手,现在竟变得如此不听使唤。然而,此时此境,吴先生仍不乏其特有的幽默慢慢地说:“这本书,想看的人传着看,不过所有权属于你。”1996年春,北京某文化艺术公司委托西藏美协以一年时间创作大型历史油画《金瓶掣签》,因考虑到主题的重大,以及作品应具备的文化审美高度,西藏自治区班禅灵童转世办公室特修函商,请与十世班禅大师生前有着珍贵友谊的吴作人先生担任《金瓶掣签》的艺术顾问(另位顾问为西藏自治区领导丹增先生)。
1996年5月中旬,西藏美协派我和另两位作者携《金瓶掣签》素描稿与色彩稿专赴北京请吴作人先生点拨指导。那日天公作美,车子出发时阵阵佛光法雨,驶抵吴府时,则现丽日碧空。只见吴作人先生在工作人员服侍下正于花木假山掩映之间闭目负暄,气色也明显的红润。我们说明来意后便和工作人员一同推吴先生到了那间画室兼客厅的大房间,我无意间发现吴先生画案的位置已摆放着一架钢琴,前面又堆着一沓沓的书籍画册,心里默默地想,难道吴先生再不需要,再无可能在那张铺着薄毛毯的画案上点染江山了吗?事实是无情的,此时的吴先生那一线仅存的视力几乎变成了一丝,且听力也更微弱了。
我们在他老人家面前徐徐展开画稿然后由我大声地向他说着画面的布局,人物的组合,色彩的处理及要追求的西藏绘画的旨趣。吴先生边听边反射性地双手合十,缓缓地说:“很好,很有意义,缘分……”这时萧先生在旁解释道,“文革”结束后,十世班禅曾特意来家看望过吴先生,当时班禅大师坐的位置正好是你们画稿这里。我们才恍然大悟。
此时此境,一位美术界的泰山北斗居然靠听一个后生小子夸夸其谈后方能参与一件作品的创作指导,怎不令人叹息。我说完后轻轻握住吴先生那仍是合十状的柔软的双手,不禁联想到奥地利小说《看不见的收藏》里的主人公,尽管我极不忍心将之与敬爱的吴作人先生联系在一起,但我实在无法排遣与回避眼前的事实。
1997年3月底,《金瓶掣签》如期完成并获有关部门审查通过,后来还获得西藏自治区政府奖。我们三个作者希望早日带着这幅塑造了126个西藏僧俗各界形象的大幅油画赶赴北京,赶赴四季花香与绿荫同在的西郊花园村华侨公寓,去向调养中的吴作人先生汇报创作得失并企望再次得到他的教诲。我们不止一次地在拉萨默祈他老人家能够康复,能够出现奇迹。然而北京方面的送画通知一等再等,到4月初竟完全失去了联系。谁知4月10日晚间从电视新闻中竟得知敬爱的吴作人先生飘然仙逝的噩耗。一代大师,没能见到他一生中最后参与指导的作品的完成面貌。这到底是遗憾,还是吴先生那伴随大半生的西藏情结的最终句号呢?又有谁人能够说清。
吴作人先生生前曾给西藏美协一幅上世纪60年代手书的毛泽东词:“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人生终归是极其有限的,连同我们所赖以生存的高山巨川,乃至于星球宇宙也都各有其尽时。那么究竟什么可以长存与不朽呢?大概唯有人们常常津津乐道的某种精神吧。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西藏美协主席)
编辑:邢贺扬
关键词:韩书力 吴作人 西藏情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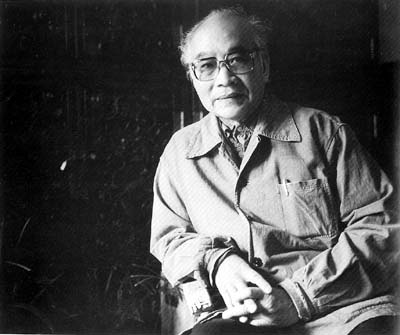


 贵阳机场冬日为客机除冰 保证飞行安全
贵阳机场冬日为客机除冰 保证飞行安全 保加利亚古城欢庆“中国年”
保加利亚古城欢庆“中国年” 河北塞罕坝出现日晕景观
河北塞罕坝出现日晕景观 尼尼斯托高票连任芬兰总统
尼尼斯托高票连任芬兰总统 第30届非盟首脑会议在埃塞俄比亚开幕
第30届非盟首脑会议在埃塞俄比亚开幕 保加利亚举办国际面具节
保加利亚举办国际面具节 叙政府代表表示反对由美国等五国提出的和解方案
叙政府代表表示反对由美国等五国提出的和解方案 洪都拉斯首位连任总统宣誓就职
洪都拉斯首位连任总统宣誓就职
 法蒂玛·马合木提
法蒂玛·马合木提 王召明
王召明 王霞
王霞 辜胜阻
辜胜阻 聂震宁
聂震宁 钱学明
钱学明 孟青录
孟青录 郭晋云
郭晋云 许进
许进 李健
李健 覺醒法師
覺醒法師 吕凤鼎
吕凤鼎 贺铿
贺铿 金曼
金曼 黄维义
黄维义 关牧村
关牧村 陈华
陈华 陈景秋
陈景秋 秦百兰
秦百兰 张自立
张自立 郭松海
郭松海 李兰
李兰 房兴耀
房兴耀 池慧
池慧 柳斌杰
柳斌杰 曹义孙
曹义孙 毛新宇
毛新宇 詹国枢
詹国枢 朱永新
朱永新 张晓梅
张晓梅 焦加良
焦加良 张连起
张连起 龙墨
龙墨 王名
王名 何水法
何水法 李延生
李延生 巩汉林
巩汉林 李胜素
李胜素 施杰
施杰 王亚非
王亚非 艾克拜尔·米吉提
艾克拜尔·米吉提 姚爱兴
姚爱兴 贾宝兰
贾宝兰 谢卫
谢卫 汤素兰
汤素兰 黄信阳
黄信阳 张其成
张其成 潘鲁生
潘鲁生 冯丹藜
冯丹藜 艾克拜尔·米吉提
艾克拜尔·米吉提 袁熙坤
袁熙坤 毛新宇
毛新宇 学诚法师
学诚法师 宗立成
宗立成 梁凤仪
梁凤仪 施 杰
施 杰 张晓梅
张晓梅


